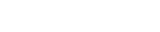东西|专访|蒋韵:每写完一个东西,总有抢救出什么的感觉( 二 )
蒋韵:如你所说 , 这两部作品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 我先动笔写《北方厨房》 , 在写到制作“土豆沙拉”蛋黄酱的时候 , 我写到了那个苏联女人 。 一个念头冒出来 , 猜想 , 她或许是我们那个内陆城市“蛋黄酱”的始作俑者 。 这已经偏离非虚构 , 开始向小说倾斜了 。 一想到小说 , 心猿意马 , 觉得这一短短章节承载不了我想表述的东西 。 于是果断放下了《北方厨房》 , 开始了《我们的娜塔莎》的写作 。
说实话 , 比起散文、非虚构 , 我更喜欢写小说 , 因为它更自由 。 也只有在小说的世界里 , 我才能够凭想象 , 从无到有 , 完成一个苏联女人和一座城市悲剧性的命运关系 。 《我们的娜塔莎》写得我心痛难抑 , 却也觉得了了一桩心事 。 接下来才又继续写《北方厨房》 。 所以 , 它们确实是相伴相生的姊妹篇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澎湃新闻:《北方厨房》前后写了多久?
蒋韵:不到三个月吧 。 我们2020年三月初从海南回到北京 , 居家隔离期间动笔 。 六月十九号完成 。 这期间还穿插写了《我们的娜塔莎》 。
澎湃新闻:还记得写完那一刻的场景吗?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蒋韵:写完那一刻的具体情景 , 不记得了 。 但 , 这几年 , 每写完一个东西 , 总有一种抢救出什么的感觉:从自己的记忆中 , 从日渐老去的生命中 。 像是和生命赛跑 。 有一点苍凉的满足感 。
澎湃新闻:我想到在《北方厨房》之前 , 你还写过一篇有关饮食和家族史的非虚构作品:《青梅》 , 它主要写的是你姥姥和母亲的故事 。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 , 你说它是写给外孙女如意的:“或许她还没长大 , 我的记忆已经如同我母亲一样死亡了 。 我想让她知道一点从前的事情 , 让她知道一点我们这个小小家族的过往 , 让她知道 , 她来自何方 。 仅此而已 。 ”那么 , 写《北方厨房》 , 是不是也有“留住记忆”的原因?
蒋韵:完全正确 。 写《青梅》时 , 确实是想为我的如意留下一份家族的备忘录 。 而写《北方厨房》 , 则是有些野心的 , 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北方家庭 , 写“吃”的历史 。 想为食物写一部史记 。 为某段历史留下“味觉记忆” 。 它应该大于一个家庭的范畴 。 大于一个地域的范畴 。 食物的千姿百味 , 如同人生的种种况味 , 有着大江大河般的壮阔和命运感 。 人记忆历史的方式是多样的 , “食物史”也许是最为烟火气 , 也是最鲜活最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 。
澎湃新闻:是的 , 对我这样一个南方读者来说 , 书里写到的“假鱼肚”“瓜菜代”“蒸菜蟒”都是非常陌生的食物 , 但读来并没有觉得隔阂 , 可见食物的滋味和体会是可以跨越地域和时间 , 可以共通的 。 总体来看 , 《北方厨房》的前五章写了家里先后三个主厨时期:奶奶主厨时期、母亲主厨时期和“我”做主厨时期 。 第六章写到记忆深处里和“吃”有关的人和地方 , 最后则是一章带有反思意味的结束语 。 这个文本结构是一开始就想好的吗?
如果说家庭饮食史是《北方厨房》的树干 , 那么那些和家人有关的插曲 , 和邻居有关的故事 , 和朋友有关的相聚就像是自由长出的枝叶 , 共同构成这部作品茂盛浓密的样子 。 尤其那些与食物无关的碎片小事 , 像是兴之所至 , 是不是写作之初没有想到的?你怎样看待它们在文本中的作用?
蒋韵:我写小说 , 特别是长篇小说 , 结构一直是我的弱项 。 我缺少宏观把控的能力 , 也没有写提纲的习惯 , 更不会像照着图纸盖房子一样建构我的小说 。 我曾在一个访谈中谈过这个话题 , 我说 , “我的小说 , 就如同原生态的乱流河 , 它永远不会限定在我最初给它挖掘的河道之中 。 它一路奔腾 , 东突西撞 , 冲毁河岸 , 随心所欲 , 自由改道 。 ”
推荐阅读
- 食物|吃 相
- 玉米|这东西再贵也要吃,拿来煲汤,鲜美营养增强免疫,孩子成长正需要
- 蔬菜|冬天,这东西见一次买一次,既是蔬菜也是水果,每次上桌都光盘
- 鱼肉|煎鱼时抹点这东西,不破皮不粘锅,鱼肉鲜嫩不腥,卖相好更美味
- 翻炒均匀|炒藕片时,边炒边加点这东西,藕片洁白不发黑,可惜很多人不知道
- 面团|蒸包子发面不要只用酵母,多放点这东西,蓬松暄软,包子白又胖
- 庄园|没用过这5件“老东西”,你的2021年就算白过了
- 饺子馅|韭菜馅饺子,最忌讳放这东西,很多人还在放,难怪吃着不香不好吃
- 妙招|香菇用清水洗是不对的,教你个小妙招,让脏东西细菌自己跑出来
- 清水|香菇用清水洗不干净?教你一小妙招,让脏东西小虫子自动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