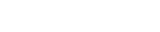东西|专访|蒋韵:每写完一个东西,总有抢救出什么的感觉( 六 )
澎湃新闻: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电影 , 叫《寻梦环游记》?它讲述了一个亡灵世界的故事:每到一年一度的亡灵节 , 逝去的灵魂都会返回人间与亲人团聚 。 但若人间无人记得这个灵魂 , 它就会灰飞烟灭 。 也就是说 , 一个人真正的死亡 , 发生于他被世人完全遗忘之时 。
蒋韵:遗憾 , 我没看过《寻梦环游记》 。 但听你的讲述 , 真是很有意思也很悲伤 。 确实 , 某种意义上 , 一个人真正死亡发生于他被世人完全遗忘的时候 。 比如我的祖母蒋宪曾 , 在我和我的弟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 她才真正地不再存在 。 因为 , 那时候 , 这个世界上 , 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她、记得她了 。 比如我的父母 , 至今 , 我女儿好像一直都不认为他们已经不在了 。 她有时会说:“姥姥昨晚来过了 。 ”我说:“你梦到姥姥了?”她回答:“不是梦 , 我分得出来 , 姥姥是真的来过了 。 ”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亡灵世界 , 那我的亲人们一定都还在 。 因为我们都在想念着他们 。
她们选择了“不忘”
澎湃新闻:说到记住与遗忘 , 我还会想到你近年小说里的主人公 。 她们都无法忘记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 都因无法救赎而自我惩罚 。 她们活着 , 也被自己的记忆折磨着 。 《晚祷》中的袁有桃 , 《水岸云庐》中的陈雀替 , 《你好 , 安娜》中的素心 , 《我们的娜塔莎》中的杜若 , 都是如此 。 你为什么特别关注这样一类人?
蒋韵:因为我身边生活着类似这样的人 , 她们在一个健忘的年代拒绝忘却 。 在多数人选择遗忘 , 选择用冠冕的理由原谅自己宽恕自己洗白自己的时候 , 她们选择了不忘 。 选择了对自己的不赦免 。 我的素心我的袁有桃是她们中的代表 , 当然是被文学加工重塑过的走向极致的代表 。 她们是小众的 , 却仿佛承担了一个时代的“罪感” 。 我无法无视她们的存在 。 她们就像是我的姐妹 。 我爱她们 。 尽管我们也许并不是同一类人 。
澎湃新闻:有时 , 她们给人感觉像是从俄罗斯文学世界里走出来的人物 , 或者说是中文世界里的“异类” 。 因为相较于西方的“罪感文化” , 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约束往往来自外部 , 如法律、习俗、风评、名誉 , 而非内心的审判 。 作为写作者 , 你一直执着于“灵魂的自我拷问与救赎” , 并甘愿与这些灵魂一起经受煎熬与折磨 , 支持你这么写的力量来自哪里?你会担心这些“罪与罚”的书写在遭遇中国经验时可能会“水土不服”吗?
【东西|专访|蒋韵:每写完一个东西,总有抢救出什么的感觉】蒋韵:不担心 。 中文世界没有“罪感文化” , 但我们有“良知”、“良心” , 有“慈悲心” 。 没有“罪感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罪感” 。 我喜欢俄罗斯文学 , 一点不错 , 我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 我承认他对我影响至深 。 但 , 我小说里的人物 , 是中国人 , 我用我的方式讲中国的故事 。 去年傅小平和我有一个访谈 , 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 他说 , 你事实上已经把偏西方化的罪与罚主题 , 融汇于更为中国化的“失去、生命悲情、苦难”的文学母题里去了 。 他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 而这也确实是我这些年的追求:这些年 , 我一直试图将中国文学传统中表达到最为极致的“生命悲情” , 化为我小说的灵魂 。 生命悲情和罪感 , 在我的小说中 , 我自己觉得并不违和 。

文章图片
《我们的娜塔莎》讲述的是一个苏联女子在北方小城的故事
澎湃新闻:到了《我们的娜塔莎》 , “拷问与救赎”本身是否也在悄然变化?之前的女主人公或失去爱情 , 或背井离乡 , 或甘于承受命运中的种种不幸 ,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虐式”惩罚 。 但到了杜若 , 她不仅反思了自己的怯弱与自私 , 还开出了一家名为“我们的娜塔莎”的俄罗斯餐馆 , 并坚持店名里要有“我们的”这个前缀:“她坚守着 , 只是让这个城市记住 , 曾经 , 有一个叫娜塔莎的女人 , 在这里活过 , 爱过 , 死过 。 ”这里 , 是否也有一个从“我”到“我们”的变化?如果有 , 这一变化是否也代表着你本人对“拷问与救赎”方式的新的理解?
推荐阅读
- 食物|吃 相
- 玉米|这东西再贵也要吃,拿来煲汤,鲜美营养增强免疫,孩子成长正需要
- 蔬菜|冬天,这东西见一次买一次,既是蔬菜也是水果,每次上桌都光盘
- 鱼肉|煎鱼时抹点这东西,不破皮不粘锅,鱼肉鲜嫩不腥,卖相好更美味
- 翻炒均匀|炒藕片时,边炒边加点这东西,藕片洁白不发黑,可惜很多人不知道
- 面团|蒸包子发面不要只用酵母,多放点这东西,蓬松暄软,包子白又胖
- 庄园|没用过这5件“老东西”,你的2021年就算白过了
- 饺子馅|韭菜馅饺子,最忌讳放这东西,很多人还在放,难怪吃着不香不好吃
- 妙招|香菇用清水洗是不对的,教你个小妙招,让脏东西细菌自己跑出来
- 清水|香菇用清水洗不干净?教你一小妙招,让脏东西小虫子自动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