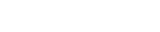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年味 , 从母亲的皮渣中走来
文 /朝君
又到了过年的时候 , 母亲早早的就打电话 , “皮渣蒸好了 , 抓紧来拿吧” 。 母亲已经八十了 , 因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 , 执拗在乡下老家住 。
祭灶节刚过 , 母亲就一遍一遍的催 , 让我们回家 , 带过年的食物 。 蒸皮渣是母亲的拿手戏 , 这种北方的食物 , 是以红薯粉团着粉条, 然后上笼蒸熟 。 那种从小滋生的味道 , 让我一想起 , 就感觉年到了 。 在众多食物里 , 只有娘蒸的皮渣 , 是我的最爱 , 所以 , 母亲每年过春节 , 都早早准备 , 为我们蒸皮渣 。
皮渣的主要食源是红薯粉和红薯粉条 。 记得小时候 , 白面短缺 , 红薯却是主要食物 。 一到冬季 , 村里家家都下粉条 。 父亲在矿山工作 , 家里缺少男劳力 , 母亲就只能让二爷、堂叔帮着下粉 。 下粉是个繁重的体能工作 , 往往一个小队才支起一口下粉的锅 , 然后排队 , 一家一家的下 。 下粉是需要好几个人集体完成的工序 , 一般都是几家早早结成组 , 多是以血缘关系近的组在一起 。 比如父子 , 弟兄 , 族人 。 当然 , 也有家庭不和睦的 , 和自己认为亲近的人组团 。 父亲只有一个姐姐 , 很早就出嫁到外村了 , 他又不在家 , 母亲就只有攀上二爷家 。 二爷家儿子多 , 弟兄四个 , 都没有父亲大 , 我全喊叔叔 。 大叔残疾 , 腿脚不方便 , 只能做辅助工作 , 三叔精明 , 只做眼皮子活 , 不出死力 , 只有二爷指挥着二叔、四叔两个人轮换端瓢 。 端瓢是下粉最重点的活 , 需要举起一瓢粉 , 敲打着 。 手一个姿势 , 不但累 , 而且手酸 , 是个功夫活 。 盛红薯粉的瓢是一个葫芦磕开的一半 , 俗话说的“一个葫芦两个瓢”就是指的这个 。 瓢下有几个黄豆大的小孔 , 粉从小孔里漏进开水锅里 , 就成了粉条 。 下粉前要把红薯粉捣碎 , 放在瓷盆里 , 然后 , 兑上水 , 打成糊状 。 下粉时 , 每次要盛多半瓢 , 不能溢出 。 二叔站在滚烫的开水锅一旁 , 然后一手举起瓢 , 另一只手握紧拳头 , 一下一下敲击着端瓢的手腕 , 让几条粉流从瓢底均匀流出 。 粉流到锅以后 , 遇上开水 , 很快就形成了粉条 。 母亲和三叔 , 轮换着把锅里的粉条捞在一尺多长的竹竿上 , 然后端出去晾晒 。 大叔在下面烧锅 。 因为其他人家都有男劳力 , 婶子们都不来这里干活 。 父亲不在家 , 母亲就顶一个男劳力 。 母亲干活手脚麻利 , 从不拖泥带水 。 她眼劲头好 , 一招一势都干得很地道 , 叔叔们没有人小看她 。 我们这些孩子们最爱凑热闹 , 挤在热锅旁看如何下粉 。 二爷哄我们走 , 一是显碍事 , 二是怕锅里的热水烫着我们 。 等下完粉 , 二爷会用碗盛出刚下的热粉条让我们吃 , 这就是我们等待的结果 。
出锅的粉条 , 需要在寒冷的天气里冻着 , 还要在挂着的粉杆撒上水 , 让粉条在粉杆上冻成一体 。 等天气好了 , 到田野里晾晒 。 这时候 , 每家每户都借着路两旁的树 , 扯好绳子 , 套好吊环 , 将粉杆一个个挂上 。 冬天的太阳真可贵 , 照在一排排粉杆上 , 将冰冻的粉条 , 慢慢的解冻溶化 。
推荐阅读
- 食材|我家从不买零食,分享6款追剧小零食,做法简单零失败,小朋友爱吃
- 大蒜|每周一景|年味
- |鸡鱼肉菜满囊中! 440多岁流亭大集年味儿浓
- 快乐|记忆里的年味儿之乡村篇
- 辣椒|从不吃辣椒的婆婆特地为女子种植一大片辣椒走红
- 自助餐|自从新冠中招后,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在我老婆身上发生
- 烧烤|重庆乡镇年味浓,老人灌香肠熏腊肉,只为子女早日归来一起团圆
- 老字号|老字号融入“新国潮”!西安饮食多款年礼让年味更浓郁~
- 古力娜扎|从此以后我也是大厨
- 河豚|东北大拉皮,我从小吃到大的家乡美食,也是我的乡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