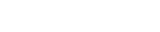最后 , 黑暗料理居然还比食堂便宜 。 花六块钱就能买到一份炒饭 , 再画三四块钱就能再买一个油炸臭豆腐之类的小吃 。 若肯花20块钱以上 , 就能吃顿烧烤了!虽然这是十多年前的往事 , 但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上海 , 这个价格 , 对自己不挣钱的我们这些学生来说 , 那真的太实惠了 。 当然 , 虽然如此生猛 。 “黑暗料理”却有一个让其闻风丧胆的天敌——城管 。3
如果你在复旦上学 , 买“黑料”的次数多了 , 你八成就会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某天 , 当你斜倚着自行车 , 等摊主给你炒饭 。 突然远方的街巷里会传来一声大吼“城管来了!”
随后 , 仿佛北欧诸神听到了末日号角吹响 , 摊主们会惊慌的张望、然后果断关火、收摊、以让你吃惊的臂力和速度 , 推着那沉重的摊位车做鸟兽散 。 说鸟兽散也不准确 , 至少在南区 , 摊主们的避难方向是相同的——他们会从属于校外的国权路、一起跑进属于学校的南区宿舍区内暂避风头 。 就跟战乱年代老百姓为了躲日本鬼子到租借逃难一样 , 跑过那条自动门的线 , 摊主们就安全了 。 于是短短不到一分钟内 , 原本热闹的整条街上就会上演一场“绝地大逃亡” , 从线那边扯到线这边 , 摊主们的移动速度 。 为敦刻尔克自豪的丘吉尔看了都要汗颜 。
然后 , 摊主们会隔着校园的栅栏向路那边张望 。 等城管的车一溜烟的经过后 。 做饭的摊主与等饭的学生 , 又会迅速“众神归位” , 骂几句城管“偷袭”了事 。 再然后 , 摊主八成会一脸歉意的跟你说:“不好意思哈 , 饭都给你炒粘了 , 不好吃了 , 要不这份算送你的吧!”毕业很久以后 , 我看一位同学写的怀念文章 , 才理解这种奇观到底为何会形成——虽然复旦在杨浦区 , 但杨浦只是个正局级的单位 , 而复旦呢?是副部级 。 所以杨浦的城管不敢到复旦校内去抓小摊贩 , 就像汤姆永远抓不住会躲到老鼠洞里的杰瑞 。
而且你说这些城管到底执法有多认真呢?这事儿也存疑 。 反正我就不止一次看过这种事情——双方这场“猫鼠游戏”玩完之后 , 城管们会把执法车找个地方一停 , 然后单人(注意 , 一定是单人 , 不会成群结队 , 估计是怕摊主误会)折回来 , 走到自己喜欢的那家摊前 , 也说上一句“哎!来个腊肉炒河粉 , 多加点腊肉哈 。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场景特魔幻——这些城管大叔 , 其实下了班也跟我们这些学生一样 , 都是手头拮据的普通人 , 甚至跟那些摊贩夫妻是比我们熟太多的朋友 , 某些摊贩卖的烤串、炒饭 , 甚至也是其爱物 。 唯一的特权 , 可能就是他们要求“多加点腊肉” , 摊主一般不会拒绝 , 而普通学生不行 。 可是尽管如此 , 每月总有那么几天晚上 , 这种午夜惊魂还是会上演 , 且若真有哪个摊主不幸没越过那道分界线 , 真的会被收走小摊 。 可这样的游戏 , 大多数情况下 , 除了做粘了几份炒饭 , 又有什么什么实际意义呢?这一切到底图啥?这些戏又演给谁看的呢?我一直想不明白 。4
临到我快毕业时 , 我看了学校一个经济学老师领着学生搞的一份研究报告 , 研究对象就是复旦的“黑暗料理界” 。 看了那篇文章我才知道 , 原来我几乎每天去吃的“黑暗料理”水很深 , 几点出摊 , 位次怎么排 , 那嗓子“城管来了”谁负责喊 , 价格怎么涨 , 甚至如果除了真出了卫生安全问题 , 摊主们为了维护“集体品牌”要对涉事者怎么处罚、怎么驱逐 , 都是有行规的 。 有些运行机制 , 甚至特别像英国中世纪晚期的行业工会 。 所以 , 这其实是一个精妙、有序、甚至有内部协调机制的小社会、小市场、甚至“自我管理体系” , 虽然看似“黑暗” , 但他们运作、并自我管理的其实非常好 。 而且这个系统创造的经济活力其实不小 。 据那份调查统计、估算 , 那些摊主们的月利润应该在8000-12000元/摊月左右 , 即便是上海 , 在十年前 , 这也相当可观了 。 更是远远高于那个年头复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 。 至少我当时 , 看了那个调查以后 , 心情就很复杂 。 那时的我刚刚找好工作 , 单位许诺的一个月工资也就每月五千(其实后来很长时间都没达到) 。 所以我特别眼馋给我炒饭的那位大叔——这么多年 , 我读书 , 您炒饭 , 原来闹了半天 , 您才是真正的“中产”啊 。 于是 , 最后几天吃他的炒饭时 , 已经混熟了的我俩说起这事儿 。 我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要不然以后我也来跟您学炒饭也不错啊 , 是门手艺 。 印象中 , 大叔难得的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 然后专心继续颠勺 。 只是间或拿毛巾擦汗的时候 , 咕咕噜噜的说了我几句:小伙子上这么好的学校 , 爹妈供你读了这么多年书 , 还是找个体面工作好 。 再说 , 这苦 , 你们这些娃 , 未必吃得了 。 这些话 , 他说的虽然含混 , 但我记的却清晰——我大学的那些年里 , 是这些阿姨大叔 , 深更半夜替我做饭 , 用一份份加量不加价的炒饭 , 喂饱了我辘辘饥肠 。 但我并不需要感谢他们 , 想来 , 他们也不需要我为他们的辛勤致谢 。 因为我们每一次的交易 , 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饭”的公平自由交易:多年买饭时的等待 , 让我知道卖烧烤的那位小哥当时正在攒钱买房子 , 而那对炒饭的叔叔阿姨有两个在读大学的孩子、生活压力挺大 , 那位炸豆腐的大叔的儿子则快娶亲了 , 对方要的彩礼费 , 得像那一块块油炸豆腐一样 , 由他从滚烫的油锅里捞起来……所有这些人 , 起早贪黑、推食食我、把饭做的又好吃又便宜还安全 , 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理由 , 而只是为了挣他们的营生、过他们日子 。 这一切正如 ,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的那般:“我们并不是借由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的 , 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不要向他人乞求怜悯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不要向他人谈自己的需要而是只谈对他们的好处 。 ”
推荐阅读
- 课堂|联合拍摄原生态乡村美食制作短视频,青岛这所大学将课堂“搬进”农家
- 小巷|巷子里的叫卖声
- 鸡蛋|位置特殊只卖1.5小时,就这小吃竟送走了两届毕业生
- 产品|无糖饮料时代,冰峰拿什么留住消费者?
- 烙饼|为什么上了大学后,大家纷纷开始买锅做饭?
- 尹波|足不出校品美食 湖南中医药大学举行首届美食文化节
- 木耳|每天400斤玫瑰花30多个菜品,这所大学的玫瑰宴馋哭网友
- 饺子|一女子去韩国留学,晒出大学食堂饭,网友:潲水桶都比这有食欲
- 玫瑰花|好看又好吃!云南大学每天400斤玫瑰花端上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