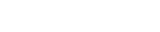糍粑|杨德振:家乡的糍粑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每逢在广州过年 , 在湖北老家的亲戚朋友总会问我“最想吃家乡的什么食物?寄些过来;”我总是回答说:“要寄就寄糍粑吧!别的不需要了 。 ”家乡的糍粑不仅是年味的一种重要具象和形式呈现 , 更成了我们在外游子的乡愁挥发的载体;吃上家乡黏黏的糍粑 , 味蕾顷刻间被故乡的谷物唤醒 , 唇齿间沾满的是故乡的香甜与绵长记忆 , 与故乡的山高路远、山水阻隔的愁绪仿佛一下子得到了消解和融化 。
【糍粑|杨德振:家乡的糍粑】在故乡湖北麻城 , 糍粑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 , 可是“奢侈”食品 , 每个人只有过年才能够吃上 。 改革开放后这种“奢侈”食品才变得很平常和普通 , 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吃到 。 但是 , 人们并不会因为食品的平常和普通而减少对它的青睐和喜好 , 它已成为大别山地区农民的一个集体记忆符号 , 蕴藏着在艰苦年代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和向往;人们吃在嘴上 , 感恩时代赐予的甜蜜与幸福却在心里开了花 。
我小时候是在大别山里度过的 ,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 家里只有到过年时才从生产队称回七、八十斤糯谷 , 父亲挑上糯谷去村里碾成米 , 回来由母亲把糯米中的谷糠筛掉 , 剩下大概五十斤的糯米 , 放在水桶里浸泡两天两夜;然后 , 等到腊月二十八制作糍粑 。
大别山农村有“二十八 , 打糍粑”的俚语和说法 , 左邻右舍的男人便合伙去抬来一个大石臼 , 放在稻场中;这时候 , 村里家家户户便飘散出蒸糯米的香味 , 此时也是我们小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候 。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吃到蒸熟的糯米团子 , 还可以看到大人们打糍粑时的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欢笑声 , 声浪一声高过一声 , 童稚声、欢乐声在稻场上飞扬 。
打糍粑一般需要四个人共同完成 。 大家用树棍子在石臼里捅搅 , 糯米在石臼里“卟噗、卟噗”地叫个不停 , 仿佛温泉冒泡的声音;大概半小时后 , 所有糯米已捣碎 , 融化成一个大面团 , 四个人便把树棍旋转走上几圈 , 把面团架起来 , 举的高高的 , 撂在门板上;母亲在门板上早已撒上了面粉 , 接下来 , 她一边用手沾上温开水 , 慢慢开始把糯米团按平;整个长方形的门板上 , 一大块糍粑基本上就成型了 。
摊晾一、两天后 , 糍粑脱水、干硬了 , 再用菜刀切开 , 划成书本那么大齐齐整整的方块型状;父亲则挑来清澈、冰冷的井水 , 倒在一口大缸里 , 母亲把一块块方形糍粑放进大缸里 , 想吃的时候 , 就去缸里取;整个春节里 , 用糍粑搭配面条、腊肉招待上门拜年的客人 , 这在当时是最好客的一种表现 , 也是最为隆重一种待客形式 。
这时的糍粑 , 我们小孩子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 , 只有等父母招待客人时 , 客人吃不下那么多糍粑 , 便“回碗”(剩下的意思) , 那就成了我和我妹妹、弟弟大快朵颐的食物;有时候 , 客人全部吃完了 , 让我和妹妹、弟弟很“失望”和伤心;现在想起来 , 是又好笑又心酸 。
有时候 , 我和妹妹、弟弟偷偷把水缸里的糍粑捞起 , 放在灶炉的火灰里烤灸 , 总想瞒住父母 , 父母一看我们兄妹几个齐齐整整地坐在厨房的灶膛边 , 帮忙添柴把火 , 做家务事的“劲头”高涨 , 明白了我们肯定在灶膛里“捣腾”吃的东西 , 假装没看见......糍粑烤好后 , 我们小家伙用柴火棍棒夹起糍粑就往外跑去 , 偷偷吃起来 。
推荐阅读
- 面包|我家乡的特色面食
- 奶茶|咸豆花还是甜豆花?别争了!还是我家乡富顺的豆花最好吃
- 巧克力|年夜饭上的那杯“酒”:是青春的过往,也是浓浓的家乡情
- 糍粑|口水直流的2种经典糍粑,简单好做,外焦里糯,赞不绝口
- 糍粑|新春走基层|淄川:传统年糕旺销
- 河豚|东北大拉皮,我从小吃到大的家乡美食,也是我的乡愁所在
- 糍粑|黄花菜炖牛肉
- 汾酒|不管离家多久,年夜饭上的那杯“酒”,就能拉近你与家乡的距离
- |这块肉卷制作是在家乡特色美食豆腐卷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味道真棒
- 八宝饭|家乡烟火味,最抚行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