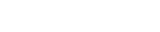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场团圆 , 人们在吃吃喝喝中 , 不咎既往 , 充实希望 , 端起的酒杯与祝福的话语融汇交错 , 我们称其为——年味儿 。
老家过年有吃头肉的习俗 , 寓意着新的一年从头开始 。 头肉的选择范围有限 , 无非是猪头、羊肉和牛头 , 谁要敢说过年吃鸡头 , 估计旁的人一巴掌能拍死你 。
头肉只允许煮一颗 , 羊头肉太少 , 不够一家人吃 , 自然被剔除掉 。 牛头肉不易得 , 在以畜力为主的年代 , 牛是家庭中的一员 , 老了也不会宰杀 , 当然 , 兜比脸干净的乡亲们也没有替它养老的自觉 , 一般是卖给牲口贩子挣点钱 , 丝毫不顾老牛临走时的一步三回头的依恋和眼里流出的泪水 。
贫穷之下 , 泪水是最无情最无用的东西 。 再者说来 , 老人们也不愿意吃牛头肉 , 在古代 , 除了老病而死的牛 , 宰牛是不被允许的事情 , 虽然我儿时牛已经渐渐成为肉类的提供者逐步退出耕种的舞台 , 可老人们总觉着牛这东西有灵性 , 不吃为好 。 大过年的 , 人们不想拂老人的面子 , 弄出一遭不痛快来 。
猪头肉是最常见的头肉 。 冬天宰了猪 , 肉卖掉 , 头蹄下水留到大年三十 , 一锅炖 , 听着纷乱 , 看着有点点恶心 , 可吃起来那是真香 。 满口的油是新一年的希望 , 蹭到脸上也不擦 , 这叫油光满面;粘手的肉好似胶水 , 两只手指碰一下 , 拉开 , 有幸福的撕裂感 , 这叫手头粘油;老人小孩怕腻 , 吃猪头肉需要蘸醋解腻 , 一个大碗里盛上多半碗醋 , 一块猪头肉放进去 , 不仔细捞都找不到 , 这属于山西人的后代遗传下来的吃醋基因 , 姑且算是不忘本吧 。
我小时候家里过年极其热闹 。 那时爷爷奶奶健在 , 在外工作的伯伯们过了小年便和单位请假 , 携妻带子归乡 , 一大家子十多口人天天窝在一起 , 净盘算吃喝了 。 不怪人们懒散 , 忙了一年 , 好不容易能好好歇这么几天 , 抓紧时间打打牌 , 无拘无束喝点酒 , 累了热炕头上躺下 , 一会眯瞪一觉 。 待睡醒后 , 玩牌的聚在一堆 , 不玩牌的烧几暖壶开水和奶茶 , 边吸吸溜溜地喝着边聊天 。 甭看叔伯们都是几十岁的人 , 在爷爷奶奶面前 , 他们终于可以放下成年人的面具 , 没心没肺当几天孩子 , 比我们还矫情 。
除夕的年夜饭是过年的重头戏 , 需要全家总动员来操持 。 早晨起床洗漱后 , 爱做饭的四伯先给大家伙煮方便面 , 我们几个孩子帮忙撕方便面袋子 , 十几袋面下到锅里 , 袋子里的碎渣是我们的酬劳 , 一股脑倒进嘴里 , 嘎嘣嘎嘣咬的脆生 。
连汤带水的吃完面 , 肚里有了热乎气 , 胳膊腿儿有了劲儿 , 大家开始分头行动 。 大伯和二伯在院子里支个专门做饭的灶 , 他们手指粘唾沫找风向 , 垒砖搭锅一气呵成 , 据说此“娴熟”得益于他们儿时偷偷烤土豆的“基本功” , 灶搭好后 , 一天不熄火 , 炒菜全靠它 。
四伯和我父亲收拾猪头和猪蹄子 , 其实就是燎毛 。 猪头在小房里冻了许久 , 硬邦邦的好像石头 , 等它化开少许 , 四伯和我父亲一个守在炉子跟前烫炉钩子 , 一个用烧红的炉钩子在猪头上来回烙 , 他们两个人配合默契 , 两根炉钩子没有间歇 , 一阵阵“滋滋”的声响过后 , 股股青烟伴随着燎毛的气味四散 , 熏人 。
推荐阅读
- 黄豆芽|从来没想过#圣迪乐鲜蛋杯复赛#石锅拌饭还能这么做
- 芥末|上桌妙光的香菇蒸鸡,这个冬日别再错过啦
- 糯米鸡|拉丝糯米鸡
- 蒜香炒蛤蜊
- 豆芽|过年时,老人说最忌讳吃这4道菜,否则明年会越吃越穷,你知道吗
- 香辣鸭脖|过年吉祥年夜饭菜谱一定要收藏
- 糯米团|米鬼(kui)两字组成的字,还是一道过年美食?见过吗?
- 猪蹄|难怪慈禧都赞不绝口,晶莹剔透好清爽,过年没它真不行!
- 奶酪液|QQ糖奶酪
- 胡椒粉|冬天别错过这7道汤,好喝好做又易吸收,滋补不上火,还对肠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