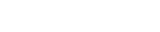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天津|饽饽姓刘】贴饽饽 , 必须得有烧柴的大锅 。 那时候 , 农家大抵只有一个灶、一口锅 , 那锅里还要熬白菜 , 饽饽只能贴在锅沿 , 饭菜一锅出 。 天津名吃贴饽饽熬鱼 , 其实并非农家菜 , 而是渔家菜 。 在农家 , 贴饽饽的标配是白菜 , 此种吃法每年要经历漫长的冬春 。
和好面后 , 玉米面子在农家主妇手中一会儿就鼓捣成了椭圆形的面饼子 , 然后就听“啪”的一声!玉米饼子被贴在了锅边 , 利用其黏性粘在锅上 , 此是谓贴 。 剩下的就是添柴烧火 , 然后揭锅开饭 。 每每此时 , 我们兄弟急急巴巴地看母亲抓起锅盖把手 , 她边揭锅边热切地说道:“揭锅就熟——饽饽姓刘!”我们开始只是傻笑 , 后来则反问:“那要是不熟呢?饽饽姓嘛?”母亲就说:“饽饽姓李 。 ”
饽饽熟时 , 我们望见热气氤氲 , 白色的气体飘浮于锅上 , 定睛一看 , 就见那锅边的一围饽饽 。 母亲所贴的饽饽 , 比其他人家所制颜色略浅 , 浅白或金黄;又因极薄 , 入味犹香 , 尤其是底部粘锅而形成的嘎儿 , 酥脆好吃 。 同样是玉米 , 不同的人贴出的饽饽 , 滋味不同 。
但是 , 玉米毕竟是粗粮 , 黏度弱 , 呈颗粒状 , 吃着掉渣儿 。 出锅时还好 , 倘若一凉 , 则硬如磐石 , 难以下咽 。 母亲仍有办法 , 她将饽饽中间以刀切开 , 涂上香油、撒上盐面 , 谓之“油盐饽饽” 。 这是我家私家吃法 。 这样吃自然是滋味有加 , 但此法也不常用 。 这也是我们常常听说的“粗粮细作”之一种 。
但是 , “饽饽”在天津也是伤人的蔑称 , 比如说:“老王长得跟个饽饽似的!”当然这不是指老王的体形 , 因为饽饽的渣儿是颗粒状 , 而某人脸上若有粉刺、酒糟或麻子 , 便类似于饽饽 。 这个比喻虽苛刻 , 但却精当 。 天津人幽默 , 都是文学大师 。
粗粮即使细作 , 毕竟还是粗粮 , 三四十年之前 , 白面偶尔才能吃上 。 随着生活稍见起色 , 饭桌上粗细均有了 。 母亲总是吃粗粮 , 其他人则常常受到照顾 。 有一次 , 我艰难地将手伸向馒头 , 当场受到父亲的质问:“老大 , 你怎么就得吃白面呢?”我找不到理由 , 无言以对 , 羞愧难当 。 我终生难忘此事 。 彼时天津近郊农村 , 比起周围外县 , 还要强些 。 那时还有乞讨者走街串巷 , 甚至三五成群 。 几十年来 , 社会之发展变化 , 生活由贫而富 , 思之不禁恍然 。
半块乃至小块的饽饽 , 多为剩饭 , 但由此衍生出一种吃法 , 即炒饽饽——现今饭店里亦有此饭 , 加韭菜、虾皮等 , 玉米面中又添加奶制品以软化 , 食之味觉已非;而在当年 , 这实属将就之举 。 故饽饽不只论个 , 也论块 。
我还记得一件事 , 略可一记 。 我家有一捉鼠的工具 , 不是铁夹 , 而是通体木制的如同一个提盒 , 一块砖头悬在横架之上 , 老鼠踩中机关 , 那砖即会落下 。 我每每好奇 , 期冀可以看见老鼠被当场砸死 。 一日忽见一只老鼠出动 , 极想将之捉住 , 而这需要诱饵 , 就是饽饽 。 但当时我遍寻家中 , 居然无一块饽饽 。 我在情急之中 , 老鼠早已逃之夭夭 。 其实 , 这太过天真了 , 饽饽就是找到 , 光天化日的 , 老鼠又岂肯上当呢?
多年以来 , 我家早已离开农村的社会圈子 , 但总有农村的亲友仍以玉米面相赠——天津人称之为“棒子面” 。 据父母所称 , 故乡小南河村的棒子面好吃——而且小南河村有一朱姓人家 , 他家有台神奇的电磨 , 只有那台电磨所推的棒子面 , 才是最好吃的 。 我们管将玉米面去皮叫做“推磨” , 虽然并不再以人力或畜力推之 , 但仍这么称呼 。 我很疑惑 , 为什么电磨去皮 , 也可分出味道?或者这包含着乡情吧 。 但棒子面易得 , 大锅难求 , 我特意购置 , 在小院里存放 , 偶尔拾来些柴火 , 在母亲贴饽饽之时 , 默默回味着“揭锅就熟——饽饽姓刘”的口诀 , 倏忽间像回到了小时候 。
推荐阅读
- 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最出名的7道小吃,特色天津味,香甜酥脆,你都吃过几道呢?
- 星际迷航|浩瀚宇宙般的星空下午茶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携手SPACE CLUB呈现
- 发糕|天津面馆开业不到2个月,干趴整条街,日卖600碗有人跑60公里来吃
- 天津小烤饼的别样做法,吃过的人都喜欢
- 小烤饼|天津小烤饼
- 蒸菜|天津这家火锅店突然火了,8元一份生菜只有两片,网友竟站队餐厅
- 结肠癌|素菜界的香饽饽——麻婆豆腐#一学就会快手菜#
- 天津市|大喜馄饨,谁在为它造神?
- 天津市|杏鲍菇这样做比肉香,做法简单,成本只要5块钱,开胃又下饭
- 冬日|趣味体验+美食 天津意风区宝藏店铺解锁冬日新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