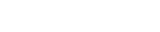жҜҚдәІ|еёёеұұж–°й—»зҪ‘дёЁжҜҚдәІйӮЈеқӣиұҶз“Јй…ұ

ж–Үз« жҸ’еӣҫ
еҸ¶й•ҝйқ’
зј–иҖ…жҢүпјҡ
жөҷжұҹеёёеұұжҳҜдёӯеӣҪйІңиҫЈж–ҮеҢ–зҡ„еҸ‘зҘҘең°гҖӮиҫЈжӨ’пјҢеңЁжҳҺжңқеҗҺжңҹдј е…ҘдёӯеӣҪпјҢзӣҙиҮіжё…жңқдёӯеҗҺжңҹдёӯеӣҪдәәжүҚејҖе§Ӣжҷ®йҒҚеҗғиҫЈпјҢеёёеұұдәәеңЁиҫЈжӨ’з§ҚйЈҹж–№йқўе Әз§°е…ҲиЎҢе…ҲиҜ•иҖ…д№ӢдёҖгҖӮжң¬жҠҘзү№жӯӨејҖи®ҫдё“ж Ҹи®Іиҝ°еёёеұұдәәзҡ„йІңиҫЈж•…дәӢгҖӮ
е°Ҹж—¶еҖҷпјҢжҜҚдәІеңЁеҘ№зҡ„еәҠеә•дёӢи—ҸдәҶдёҖеқӣиұҶз“Јй…ұпјҢиў«жҲ‘ж— ж„Ҹй—ҙеҸ‘зҺ°дәҶгҖӮжү“ејҖеқӣзӣ–ж—¶зҡ„йӮЈдёҖеҲ№йӮЈпјҢдёҖиӮЎжө“йғҒзҡ„й…ұйҰҷиҝҺйқўиўӯжқҘпјҢжҲ‘жғ…дёҚиҮӘзҰҒең°з”Ёз“ўж №иҝ…йҖҹжү’жӢүдәҶеҮ дёӢж’’еңЁжңҖдёҠйқўзҡ„и–„и–„зӣҗеұӮпјҢйЎҝж—¶пјҢзәўзәўзҡ„гҖҒе№Іе№Ізҡ„гҖҒиұҶз“Јйў—зІ’жё…жҷ°еҸҜиҫЁзҡ„иұҶз“Јй…ұпјҢжҳ е…ҘзңјеёҳгҖӮжІҫдёҖзӮ№иҲҢе°–дёҠпјҢеҸҲйІңеҸҲиҫЈпјҢдёҚз”ЁиҜҙпјҢйӮЈдҫҝжҳҜе°Ҹж—¶еҖҷжҲ‘жңҖзҲұвҖңеҒ·вҖқеҗғзҡ„зҫҺе‘ідёӢйҘӯиҸңдәҶгҖӮ
гҖҗ жҜҚдәІ|еёёеұұж–°й—»зҪ‘дёЁжҜҚдәІйӮЈеқӣиұҶз“Јй…ұгҖ‘йӮЈж—¶пјҢжҜҸеҪ“жҲ‘зў°еҲ°йӨҗжЎҢдёҠзҡ„иҸңиӮҙдёҚеҗҲиҮӘе·ұзҡ„еҸЈиғғж—¶пјҢдҫҝдјҡеҫҲиҮӘ然ең°й’»иҝӣеәҠеә•дёӢеҒ·еҒ·жү“ејҖеқӣзӣ–пјҢзҶҹз»ғең°и§ЈејҖз»‘еңЁеқӣеҸЈеӨ„зҡ„з»ізҙўпјҢжүҜдёӢеҜҶе°ҒеёғпјҢз”Ёз“ўж №иҲҖдёҠдёҖеӢәиұҶз“Јй…ұгҖӮеҗғйҘӯж—¶пјҢеӨ№дёҖз®ёж”ҫеҳҙйҮҢпјҢйІңдёӯеёҰиҫЈд»ӨжҲ‘зҡ„иғғеҸЈйЎҝејҖпјҢдёҖеӨ§зў—зұійҘӯпјҢдёүдёӢдә”йҷӨдәҢиў«жҲ‘е’ҪдёӢдәҶиӮҡгҖӮеҪјж—¶пјҢи®ёеӨҡдәә家зҡ„з»ҸжөҺжқЎд»¶йғҪдёҚеҜҢжңүгҖӮеҲқдёӯжҜ•дёҡеҫ…дёҡеҘҪдәӣе№ҙзҡ„еӨ§е§җеңЁе®¶з…§йЎҫзқҖжҲ‘е’Ңдёүе§җпјҢжҲ‘们е§җејҹд»Ёзҡ„ж—ҘеёёејҖй”Җдё»иҰҒжқҘжәҗдәҺйӮ»еҺҝеұұжқ‘е°ҸеӯҰд»»ж•ҷзҡ„зҲ¶дәІжҜҸжңҲжұҮе…Ҙ家дёӯзҡ„дёҖзӮ№зӮ№з”ҹжҙ»иҙ№гҖӮжҲ‘е’Ңдёүе§җеҪ“ж—¶иҝҳеңЁеҝөе°ҸеӯҰпјҢжҜҸж¬Ўж”ҫеӯҰеӣһ家еҗғйҘӯпјҢеӨ§е§җз«ҜдёҠйӨҗжЎҢзҡ„вҖңдҪіиӮҙвҖқеҮҶжҳҜдёҖеӨ§зӣҳиў«еҲҮеҫ—еӨ§еқ—еӨ§еқ—з…®еҫ—зғӮзҶҹзҡ„еҶ¬з“ңжұӨпјҢжҠ‘жҲ–дёҖеӨ§зӣҳзәўзғ§иӮүиҲ¬зҡ„иҖҒеҚ—з“ңпјҢйӨҗйӨҗеҰӮжӯӨгҖӮжҲ‘еҝғйҮҢеҳҖе’•пјҢеӨ§е§җдёәд»Җд№ҲиҰҒиҝҷиҲ¬вҖңеҒҡ家вҖқе‘ўпјҹпјҲеҒҡ家пјҢеёёеұұиҜқ:е°Ҹж°”зҡ„ж„ҸжҖқпјүгҖӮзЁҚеӨ§дёҖдәӣзҡ„ж—¶еҖҷпјҢжүҚжҳҺзҷҪеӨ§е§җеҪ“ж—¶зҡ„еҒҡжі•жҳҜжңүеҘ№зҡ„иӢҰиЎ·зҡ„вҖ”вҖ”зҲ¶дәІеҪјж—¶еңЁйӮ»еҺҝд»»еұұжқ‘ж•ҷеёҲж—¶зҡ„е·Ҙиө„е…¶е®һжҳҜеҫҲдҪҺзҡ„пјҢжҜҸжңҲд№ҹе°ұдёүеҚҒжқҘеқ—жӯ»е·Ҙиө„пјҢйҷӨеҺ»еӨ§йғЁеҲҶжұҮ家дёӯпјҢеү©дёӢзҡ„ж—ўиҰҒз®ЎйҘӯиҝҳеҫ—з®ЎзғҹгҖӮе№ҙй•ҝжҲ‘们дёҖеӨ§жҲӘзҡ„еӨ§е§җиҮӘ然жҜ”жҲ‘们жҮӮеҫ—зҲ¶жҜҚж··ж—Ҙеӯҗзҡ„иү°иҫӣпјҢиҖҢеҪ“ж—¶пјҢеҘ№йҷӨдәҶеңЁжҲ‘们зҡ„з”ҹжҙ»ејҖж”ҜдёҠе°ҪйҮҸеҒҡеҲ°иҠӮдҝӯиҠӮдҝӯеҶҚиҠӮдҝӯдәӣпјҢиҝҳиғҪжғіеҮәеҲ«зҡ„жӣҙеҘҪзҡ„жі•еӯҗеҗ—пјҹе№ёдәҸеҪ“е№ҙжҜҚдәІеӯҰдәҶй—ЁиЈҒзјқзҡ„жҙ»и®ЎпјҢж—¶дёҚж—¶жӢ…еүҜиЈҒзјқжңәеёҰзқҖе°ҸеӯҰжҜ•дёҡжІЎеӨҡд№…зҡ„дәҢе§җеҫ’ејҹдјјзҡ„еңЁеҶңжқ‘д№ЎдёӢиө°еҚ—й—ҜеҢ—жӣҝдәәдёҠе·ҘеҒҡдәӣиЈҒзјқй’Ҳзәҝжҙ»е„ҝиҙҙиЎҘ家用пјҢ全家дәәзҡ„ж—ҘеӯҗиҝҷжүҚеӢүејәеҘҪиҝҮдәҶдёҖдәӣгҖӮ
еӨҡе°‘е№ҙжқҘпјҢжҜҚдәІе§Ӣз»ҲеқҡжҢҒжҜҸе№ҙеңЁе®¶йҮҢеҲ¶дҪңдёҖеқӣиұҶз“Јй…ұзҡ„д№ жғҜпјҢд№ҹд»Қ然вҖңи—ҸвҖқдәҺеҘ№зҡ„еәҠеә•пјҢе№ҙеӨҚдёҖе№ҙпјҢд»ҺжңӘй—ҙж–ӯгҖӮиҖҢжҲ‘е§Ӣз»Ҳе№ёзҰҸ并жҜ«ж— йЎҫеҝҢең°дә«еҸ—зқҖеҘ№з»ҷдәҲзҡ„иҝҷдёҖе°–иҲҢдёҠзҡ„зҫҺе‘ігҖӮзӣҙеҲ°жңүдёҖж¬ЎпјҢжҜҚдәІеҸ‘зҺ°иҮӘе·ұзҡ„и§ҶеҠӣдёҖеӨ©еӨ©жЁЎзіҠиө·жқҘпјҢжқҘеҲ°еҢ»йҷўиў«еҢ»з”ҹзЎ®иҜҠдёәзі–е°ҝз—…ж—¶пјҢиҝҷжүҚеңЁе®¶дәәзҡ„еӨҡж¬ЎеҠқйҳ»дёӢпјҢеӢүејәеҗҢж„ҸдёҚеҶҚеҲ¶дҪңе·ҘеәҸз№Ғзҗҗзҡ„иұҶз“Јй…ұдәҶгҖӮиҖҢжҲ‘дёәдәҶиғҪ继з»ӯдә«з”ЁйӮЈдёҖеҸЈзҫҺе‘іпјҢжңүеӨ©д№ҳзқҖдј‘жҒҜзҡ„ж—ҘеӯҗпјҢжҗәеӘіеҰҮжқҘеҲ°дәҶе№ҙиҝҲзҡ„жҜҚдәІи·ҹеүҚеҗ‘еҘ№и®Ёж•ҷиұҶз“Јй…ұзҡ„еҲ¶дҪңвҖңз§ҳж–№вҖқгҖӮйӮЈеӨ©жҜҚдәІеҫҲй«ҳе…ҙең°е‘ҠиҜүжҲ‘们пјҢе…¶е®һеҘ№зҡ„иұҶз“Јй…ұиҝҷй—ЁеҲ¶дҪңжҠҖиүәжҳҜеҘ№еҪ“е№ҙеҒҡиЈҒзјқж—¶иҺ·еҫ—зҡ„гҖӮ
жҜҸе№ҙеҶңеҺҶе…«жңҲй»„иұҶ丰收еҗҺпјҢ家家жҲ·жҲ·йғҪдјҡеҲ¶дҪңеҘҪеҮ еқӣйІңиҫЈж— жҜ”зҡ„иұҶз“Јй…ұпјҢй•ҝе№ҙи…ҠжңҲе°ұйҘӯеҗғгҖӮжҜҚдәІиҜҙиҰҒеҲ¶еҮәе‘ійҒ“йІңзҫҺзҡ„иұҶз“Јй…ұпјҢйҰ–е…ҲиҰҒеҲ¶еҮәдёҠзӯүзҡ„еҘҪй…ұй»„гҖӮеҘ№дјҡдё“й—ЁжҢ‘дәӣдёӘеӨҙйҘұж»Ўдё”йўңиүІйҮ‘й»„зҡ„е…«жңҲиұҶпјҲеҶңеҺҶе…«жңҲжҲҗзҶҹзҡ„й»„иұҶпјүеҒҡеҲ¶дҪңй…ұй»„зҡ„еҺҹж–ҷпјҢе…Ҳе°Ҷй»„иұҶжҙ—еҮҖеҶҚжөёжіЎдёҖдјҡе„ҝпјҢеҫ…иұҶзІ’е……еҲҶеҗёж”¶ж°ҙеҲҶеҸҳеҫ—иғ–д№Һд№Һж—¶пјҢеҖ’иҝӣеӨ§й”…йҮҢеӨ§зҒ«ж–ҮзҒ«з…®зҶҹпјҢ然еҗҺе°Ҷй»„иұҶжҚһеҮәеңЁз©әж°”дёӯиҮӘ然жҷҫеҺ»дёҖйғЁеҲҶж°ҙд»ҪпјҢеҶҚжҢүдёҖе®ҡжҜ”дҫӢеҖ’дәӣйқўзІүиҝӣеҺ»з”ЁжүӢжӢҢеҢҖпјҢеҪ“йў—йў—иұҶзІ’иЎЁйқўиЈ№ж»ЎйқўзІүж—¶пјҢеҶҚеҖ’е…Ҙеӣӯз°ёз®•йҮҢж‘ҠејҖпјҢ并еңЁе…¶дёҠйқўеҺҡеҺҡең°зӣ–дёҠдёҖеұӮеұұдёҠйҮҮжӢ®жқҘзҡ„йІңе«©зҡ„й»„иҚҶжһқеҸ¶гҖӮеҮ еӨ©еҗҺпјҢеҫ…еңҶз°ёз®•йҮҢзҡ„й»„иұҶиә«дёҠеёғж»ЎжҜӣз»’з»’з»Ҷз»Ҷзҡ„зҷҪжҜӣж—¶пјҢжӯӨж—¶дҫҝдјҡе°Ҷж‘ҠеңЁеңҶз°ёз®•йҮҢеҠ©зғӯеҠ©еҸ‘й…өзҡ„й»„иҚҶжһқеҸ¶жё…йҷӨжҺүпјҢе°ҶеңҶ簸箕移иҮіеӨ©е…¬еә•дёӢи§ҒдёҠеҮ дёӘж—ҘеӨҙпјҢеҫ…е®Ңе…Ёжҷ’е№ІеҗҺпјҢйўңиүІз»ҝй»„з»ҝй»„зҡ„дёҠд№ҳй…ұй»„пјҢдҫҝз®—еҲ¶дҪңе®ҢжҲҗдәҶгҖӮ第дәҢжӯҘпјҢзІҫйҖүиҫЈжӨ’гҖӮжҜҚдәІжңҖе–ңж¬ўжҢ‘йҖүе‘ійҒ“йІңиҫЈзҡ„жҲ‘们常еұұеңҹз”ҹеңҹй•ҝзҡ„ж–°йІңзәўиҫЈжӨ’пјҢеҒҡиұҶз“Јй…ұеҲ¶дҪңд№Ӣз”ЁпјҢжіЁж„ҸдёҚиғҪе°ҶиҫЈжӨ’зӣҙжҺҘж”ҫе…Ҙж°ҙдёӯиҝӣиЎҢжё…жҙ—пјҢиҖҢжҳҜз”ЁеңЁжё…ж°ҙдёӯжјӮжҙ—иҝҮжӢ§е№Ізҡ„жҙҒеҮҖжҠ№еёғе°ҶиҫЈжӨ’дёҖдёӘдёӘжҸ©жӢӯе№ІеҮҖпјҢ然еҗҺе°Ҷе®ғ们еҲҮжҲҗз»ҶзўҺгҖӮ并жҢү1ж–Өй…ұй»„еӨ§иҮҙ5гҖҒ6ж–ӨзәўиҫЈжӨ’зҡ„жҜ”дҫӢзӣёй…ҚпјҢеҠ е…ҘйҖӮйҮҸзҡ„зӣҗе’Ңе‘ізІҫпјҢиҝҳеҸҜж №жҚ®еҗ„дәәзҡ„е–ңеҘҪеҠ дәӣи®ёи’ңе§ңзұізӯүпјҢеҫ…иҝҷдәӣеҗ„з§ҚеҺҹж–ҷз»ҸеҸҢжүӢе……еҲҶз»һжӢҢж··еҗҲеқҮеҢҖеҗҺпјҢдҫҝеҸҜиЈ…е…ҘеқӣдёӯдәҶгҖӮеҲ¶дҪңе·ҘиүәдёӯиҝҳжңүжңҖеҰҷзҡ„дёҖжӯҘпјҢеңЁиЈ…е…ҘеқӣдёӯиұҶз“Јй…ұиЎЁйқўж’’дёҠдёҖеұӮи–„и–„зҡ„йЈҹзӣҗпјҢ并用粗еёғе°ҶеқӣеҸЈеҜҶе°Ғз»іе„ҝжүҺзҙ§зӣ–дёҠзӣ–пјҢиҝҷж ·еҲ¶дҪңеҮәжқҘзҡ„иұҶз“Јй…ұеҗғдёҠеҘҪеҮ е№ҙйғҪдёҚдјҡеҸҳиҙЁеҸҳеқҸгҖӮжҺҘдёӢжқҘдҪ еҸӘйңҖиҖҗеҝғзӯүеҫ…дёҖж®өж—¶й—ҙпјҢеҫ…еқӣдёӯеҗ„з§ҚеҺҹж–ҷд№Ӣй—ҙеңЁзӣёдә’дҪңз”ЁдёӢиҺ·еҫ—е……еҲҶеҸ‘й…өеҗҺпјҢдҫҝеҸҜжү“ејҖеқӣзӣ–пјҢз”Ёз“ўж №е°ҶиЎЁйқўзҡ„зӣҗеұӮиҪ»иҪ»жү’жӢүдёҖдёӢпјҢдёҖеқӣзәўеҪӨеҪӨйІңиҫЈж— жҜ”зҡ„иұҶз“Јй…ұдҫҝиқ¶еҸҳиҖҢжҲҗдәҶвҖҰвҖҰ
жҺЁиҚҗйҳ…иҜ»
- зӮ’йҘӯ|еӣһеЁҳ家еҗғйҘӯжҜҚдәІеҒҡдәҶж»Ўж»ЎдёҖжЎҢиҸңпјҢжҷ’еңҲзҒ«дәҶпјҢзҪ‘еҸӢпјҡиҝҳжҳҜдәІеҰҲжңҖз–јдәә
- зүӣиӣҷ|еӣһеЁҳ家еҗғйҘӯжҜҚдәІеҒҡдәҶж»Ўж»ЎдёҖжЎҢиҸңпјҢжҷ’еңҲзҒ«дәҶпјҢзҪ‘еҸӢпјҡиҝҳжҳҜдәІеҰҲжңҖз–јдәә
- жҜҚдәІ|йҡҫеҝҳйӣӘеӨ©вҖңжү“еҶ»е„ҝвҖқ
- жҜҚдәІжІі|и’ҷзүӣLOGOз„•ж–°пјҢ22е№ҙиҒҡз„Ұд№ідёҡзҡ„еҸҳдёҺдёҚеҸҳ
- еҺЁеёҲ|д№Ўеңҹж•Јж–ҮпјҡжҜҚдәІзҡ„зғҷйҰҚ
- йғҪеёӮеҘіжҠҘ|жҲ‘зҡ„еҶ¬иҮіж•…дәӢ/жҜҚдәІзҡ„жұӨйқў
- иҖҒжҜҚдәІ|иҝҷжҳҜжҲ‘еҗғиҝҮе…Ёе®Үе®ҷжңҖеҘҪеҗғзҡ„#дёҖеӯҰе°ұдјҡеҝ«жүӢиҸң#дә”йҰҷй”…е·ҙ
- еҶң家иӮҘ|жҜҚдәІзҡ„иҫЈжӨ’
- й…ёиҸң|и…Ңй…ёиҸңзҡ„еӯЈиҠӮеҲ°дәҶпјҢжҜҚдәІз”ЁдәҶ30е№ҙзҡ„й…Қж–№пјҢдёҚз”ЁеҠ зӣҗпјҢдёҖе‘ЁеҗҺй…ёи„ҶйҰҷ
- еӨ§зұі|жҜҚдәІзҡ„йқўзӮ•йёЎпјҲдёҖпј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