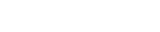祖母的一生致力于制造炊烟 。
她不习惯用打火机点火 , 而是用火柴 , 在长条形的黑色涂面轻轻一抹 , 火苗蹿起 , 点燃了黄褐的杉树枝 。 火苗之上 , 坐着一个炉 , 炉用结实的梭筒吊着 , 祖母盘着粑粑头 , 脸飘在浓烈的烟雾之中 。 她悄无声息地把柴喂进炉膛 , 无声地择菜、切菜、炒菜 。 另一个炉子的大锅里 , 煮着掺杂了菜叶剩饭的猪食 。 大小锅中间嵌着两个瓮坛 。 饭香了 , 瓮坛里的水也热了 。 舀两勺倒进放了毛巾的脸盆里 , 用热热的毛巾把脸、耳后和脖梗仔细擦干净后 , 祖母才开始炒菜 , 镬铲叮叮哐哐地响着 , 我们肚里也跑起了火车 , 写字的手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 鼻子朝蒸汽冒出的地方擤动 。
“恰饭咯!”祖母这样呼唤时 , 我们几乎是跑到饭桌旁的 。 “没人跟你们抢 , 急什么呢?”听祖母说 , 捏筷子可以预测女孩子以后离娘家的远近 , 我就偷偷把手移到筷子的下端 。 菜是家常菜 , 见荤腥的日子不多 , 除了过年 , 平日里能受到特殊优待的只有两日:一日是生日 , 寿星可吃一碗卧着两个荷包蛋的面条;另一日便是开学 。
【水也|炊 烟】祖母自己没读过书 , 独子也因家庭成分的牵连只读到高小 。 祖母深以为憾 , 便把家道中兴的希望寄托到我和妹妹身上 。 没进过一天学堂的她 , “蠢子数”(心算)却特别厉害 , 与祖父成婚后 , 除了操持家务 , 她还帮忙打理好几家店铺 。 账房先生的算盘珠子噼啪未落 , 她就已经笑呵呵地找好了零钱 。 祖母还爱哼曲儿 。 我很小就懂得忧愁 , 怕黑 , 睡觉总不安稳 , 夜里有时醒来 , 听见身旁祖母轻轻的歌声 , “……为救李郎离家园 , 谁料皇榜中状元……”她的歌声 , 在昏黄的灯光下 , 传到被褥中我的耳朵里 , 有种说不清的情愫:软软的、柔柔的 , 旁边妹妹的手也柔柔的、软软的 。
炊烟又照常升起 。 吃完饭 , 我会从炉膛里拨拉出几根没烧完的小树枝 , 练习当天学堂先生新教的字 。 不一会儿 , 地上就爬满了歪歪扭扭的“小虫” 。 祖母不识字 , 眼睛盯着“天书” , 手上的活不停 。 我知道祖母不识字 , 这便成为一场表演 。 我得意洋洋地跟她介绍:“这是‘家’ , 屋檐下面一头猪就叫家 。 ”祖母回:“这是大户人家 。 ”我说:“周围四方方 , 玉在中间藏 。 是‘国’字 。 ”祖母笑:“这还是大户人家 。 ”“那这一长串呢?”“这是《女驸马》的戏词 , 等我长大了 , 也要当状元 , 就在戏台两侧的幕布上 , 写上翁妈的名 。 ”
这个“承诺”没来得及实现 。 首先叛逃的是戏院 , 它在声光电影之中迅速缴械投降 。 戏班子离开了小镇 , 花旦留下来 , 开了个小卖部 , 用不再娇柔的声音招徕顾客 。 紧接着 , “背信”的是祖母 , 她在一个冬天脚步匆忙地走了 , 在我拿回全优的毕业成绩单之前 。
时间的蛛网结在椽木与房梁之间 。 一年四季 , 蹒跚地从祖母和我们的眼前爬过 。 祖母坟前 , 后来长了一棵小树苗 。 每年开春 , 都会抖擞出一串串小花 , 花儿像祖母纳鞋底的锥子的样子 , 攒成一团 , 掩映在更加翠绿的枝叶里 , 像炊烟一般 , 让人看不真切 。
推荐阅读
- 面包|陈香味究竟是什么味?仓味、烟味、酸味是普洱老茶该有的味道吗?
- 淡水鱼|家里有孩子多吃这菜,锅里一蒸就熟,油烟少不油腻,好吃还不上火
- 鸡翅|鸡翅不用油炸,却比油炸还好吃,外焦里嫩,健康无油烟
- 芋头|排骨别总炖,加入豆豉蒸一蒸,鲜嫩可口,少油烟更健康
- 葱末|外卖点多了,仿佛已经丧失了烟火味,一碗“水煮肉片”送给自己
- 段里|交广会客厅|烟火里的本心
- 米之炊|蒸螃蟹时,用热水还是冷水?许多人做错,难怪蟹黄外流,腿掉一锅
- 酱油醋|下饭神器无油烟傻瓜烤鱼,拌饭还能吃三碗
- 烤鱼|无油烟傻瓜烤鱼
- 油渍|油烟机油盒难清理?教你一招正确清洁油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