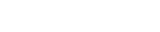客人|吃鸡、松茸、手抓羊肉,给人类学家带了怎样的考验?( 三 )
吃鸡的技术、记忆与心得
作者丨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
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 , 伴随着身体成长的是缺衣少食的大集体年代 , 肉食是个稀缺品 。 牛作为集体所有的生产力 , 杀来吃肉那是犯罪 。 尽管家里能养猪 , 但也不能随意宰杀 , 即便逢年过节 , 有了杀猪过年的理由 , 还必须交出一半给城里的供销社 , 接受国家剪刀差低价格的收购 , 或许那是一种农业重税 。 那个年代 , 对于生活在贵州偏远乡村的我而言 , 牛肉猪肉是奢侈品 , 只有在祭祀的场合 , 才有机会吃上牛肉 。 尽管那时牯藏节祭祖、扫寨等属于非法活动 , 但人们到了祭日还是会悄悄杀牛祭祀 , 沿袭千年的祖先惯习 , 谁也不敢违拗 。 万一被政府官员发现 , 众口同声:“牛自己不小心 , 昨天摔死的!”
鸡与牛、猪不同 , 生产力算不上它 , 农业税好像也没把它看上眼 , 总之用西南官话说不论公鸡母鸡都算不上“鸡的乒”(GDP) , 于是 , 即使在那个家庭个体经济非法的年代 , 有青山绿水的苗寨 , 鸡有了自由生长的空间 。 更何况鸡在苗族社会中是个不可或缺的祭物和食物 。 苗族祖先老早就把与他们生活世界中紧密关联的可食家禽、家畜和英雄祖先一起摆放到史诗里 , 其中公鸡的故事与射日的故事纠结在一起 。 传说在十二个太阳挂在天上没日没夜灸烤着大地 , 热得世间万物不能生存的时候 , 有后羿气概的苗人英雄祖先勾耶射掉了其中的十一个太阳 , 余下的那一个太阳再也不敢出来 , 世界陷入一片漆黑 , 万物不能生长 , 人类没法生活 。 万物只能施千方使百计去请太阳出来 。 马去叫不出来 , 牛去叫不出来 , 猪去叫不出来 , 鸭、鹅去请也不出来 , 最后是公鸡去叫 , 太阳脸红彤彤地走出来 。 从此 , 宇宙有了生命 , 公鸡也 合法获得了施日的身份 , 每天是它鸣叫请太阳东升送太阳西落 。 鸡也因此成为苗族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祭品、食品 。 丧葬上 , 年节中 , 立房建屋 , 婚礼 , 乃至为病重者行治疗仪式 , 甚或探望体虚伤病的亲朋 , 等等 , 无不有鸡的贡献 。 以至生出用鸡、吃鸡的民族地方逻辑 。
“鸡鸭八块”是我自小被规训的吃鸡伦理 。 所谓“八块”是指一只整鸡煮熟后切割时要保留完整的八块:鸡头、鸡腿、鸡翅、鸡脚和内脏(心肝) , 每一个部位对应分给围桌而坐的人 , 鸡头是男主人的 , 鸡肝、鸡心给最年长的 , 鸡腿给年龄最小的 , 翅膀是给已经在外闯荡或即将远走高飞的人 , 双脚是给能挣钱或希望能赚钱的人吃的 。 这是杀鸡待客或年节喜庆时吃鸡的逻辑 。如果一直生活在家乡的苗寨里 , 一个人一生中总有那么几年常被分吃鸡的某个部位 , 定会吃出技术、吃出心得来 。 当然 , 一个人从吃鸡腿到吃鸡心、鸡肝 , 也就行将走完人的生命旅程 。
在我的记忆中 , 至十七岁离开家乡上大学以前 , 吃鸡大多还是在各种祭祀的场合中 。 依稀记得那是1975年8月前后 ,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 , 吃鸡的次数特别频繁 。 那段时间 , 公鸡刚过夜晚八九点钟就高声鸣叫 , 反常的鸣叫造成了村寨人们的恐慌 , 按照当地习惯 , 反常带头鸣叫的公鸡要被斩杀祭神 , 而且会用竹签穿着它的头插到高高的山上 , 惩罚它好好看日出日落 , 知道自己是怎么犯错的 。 今天带头鸣叫的鸡被杀了 , 明天又有带头的 , 我家七八只公鸡就这样被杀掉了 , 寨子里其他人家也大多如此 。 不知过了多少天 , 有聪明的村民才提醒:“是不是电灯惹的祸?”原来 , 那段时间是村里刚建好的小水电站发电送电的日子 , 第一次用上电灯的村民兴高采烈 , 大多也不会关闭电灯 , 屋里屋外 , 通宵达旦被电灯照如白昼 , 公鸡分不清是天刚黑不久还是快要天亮 , 造成了鸡的生物钟紊乱 。 就这样我家乡有一批雄壮的公鸡为 村寨的电灯付出了生命 , 成全我们密集吃肉的日子 。 唯一幸庆的是不管何种原因 , 在贫困年代有更多吃鸡的机会 , 练就了穷日子吃鸡的技术 。
推荐阅读
- 咖啡店|咖啡店分三种:星巴克们、瑞幸们和即将死亡的小咖啡店
- 鸡胸肉|教你10道家常红烧菜的做法,两天不吃就馋得慌,客人吃了连连夸赞
- 新世界|?“虎”形头枕、年货礼盒……南京路步行街“新年集市”带你提前过年
- 老抽|酱油、生抽、老抽和蚝油该怎么用?
- 植物肉|它被称为“植物肉”,几块钱做一盘,健脑补钙、好消化,一口能下3碗饭!
- 集市|虎元素、老字号还有进博同款,南京路上的新年集市带你提前过大年
- 菠菜|日本上班族推爆的居酒屋10大排行,鸟贵族、矶丸水产你爱哪一家?
- 面包|陈香味究竟是什么味?仓味、烟味、酸味是普洱老茶该有的味道吗?
- 春寿眉|从芽头、叶片到茶梗,教你分辨白牡丹饼与春寿眉饼,很全很详细
- 烧烤|这家大牌档扎根集美11年,开在学校边,每次集会都来这,海鲜、烧烤、川菜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