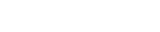毡房|吃鸡、松茸、手抓羊肉,给人类学家带了怎样的考验?( 三 )
鸡与牛、猪不同 , 生产力算不上它 , 农业税好像也没把它看上眼 , 总之用西南官话说不论公鸡母鸡都算不上“鸡的乒”(GDP) , 于是 , 即使在那个家庭个体经济非法的年代 , 有青山绿水的苗寨 , 鸡有了自由生长的空间 。 更何况鸡在苗族社会中是个不可或缺的祭物和食物 。 苗族祖先老早就把与他们生活世界中紧密关联的可食家禽、家畜和英雄祖先一起摆放到史诗里 , 其中公鸡的故事与射日的故事纠结在一起 。 传说在十二个太阳挂在天上没日没夜灸烤着大地 , 热得世间万物不能生存的时候 , 有后羿气概的苗人英雄祖先勾耶射掉了其中的十一个太阳 , 余下的那一个太阳再也不敢出来 , 世界陷入一片漆黑 , 万物不能生长 , 人类没法生活 。 万物只能施千方使百计去请太阳出来 。 马去叫不出来 , 牛去叫不出来 , 猪去叫不出来 , 鸭、鹅去请也不出来 , 最后是公鸡去叫 , 太阳脸红彤彤地走出来 。 从此 , 宇宙有了生命 , 公鸡也 合法获得了施日的身份 , 每天是它鸣叫请太阳东升送太阳西落 。 鸡也因此成为苗族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祭品、食品 。 丧葬上 , 年节中 , 立房建屋 , 婚礼 , 乃至为病重者行治疗仪式 , 甚或探望体虚伤病的亲朋 , 等等 , 无不有鸡的贡献 。 以至生出用鸡、吃鸡的民族地方逻辑 。
“鸡鸭八块”是我自小被规训的吃鸡伦理 。 所谓“八块”是指一只整鸡煮熟后切割时要保留完整的八块:鸡头、鸡腿、鸡翅、鸡脚和内脏(心肝) , 每一个部位对应分给围桌而坐的人 , 鸡头是男主人的 , 鸡肝、鸡心给最年长的 , 鸡腿给年龄最小的 , 翅膀是给已经在外闯荡或即将远走高飞的人 , 双脚是给能挣钱或希望能赚钱的人吃的 。 这是杀鸡待客或年节喜庆时吃鸡的逻辑 。如果一直生活在家乡的苗寨里 , 一个人一生中总有那么几年常被分吃鸡的某个部位 , 定会吃出技术、吃出心得来 。 当然 , 一个人从吃鸡腿到吃鸡心、鸡肝 , 也就行将走完人的生命旅程 。
在我的记忆中 , 至十七岁离开家乡上大学以前 , 吃鸡大多还是在各种祭祀的场合中 。 依稀记得那是1975年8月前后 ,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 , 吃鸡的次数特别频繁 。 那段时间 , 公鸡刚过夜晚八九点钟就高声鸣叫 , 反常的鸣叫造成了村寨人们的恐慌 , 按照当地习惯 , 反常带头鸣叫的公鸡要被斩杀祭神 , 而且会用竹签穿着它的头插到高高的山上 , 惩罚它好好看日出日落 , 知道自己是怎么犯错的 。 今天带头鸣叫的鸡被杀了 , 明天又有带头的 , 我家七八只公鸡就这样被杀掉了 , 寨子里其他人家也大多如此 。 不知过了多少天 , 有聪明的村民才提醒:“是不是电灯惹的祸?”原来 , 那段时间是村里刚建好的小水电站发电送电的日子 , 第一次用上电灯的村民兴高采烈 , 大多也不会关闭电灯 , 屋里屋外 , 通宵达旦被电灯照如白昼 , 公鸡分不清是天刚黑不久还是快要天亮 , 造成了鸡的生物钟紊乱 。 就这样我家乡有一批雄壮的公鸡为 村寨的电灯付出了生命 , 成全我们密集吃肉的日子 。 唯一幸庆的是不管何种原因 , 在贫困年代有更多吃鸡的机会 , 练就了穷日子吃鸡的技术 。

文章图片
电影《饮食男女》剧照 。
人类学宣称学科起源的动力之一是西方学人为了从别人的文化中反观自己和反思自己的文化 。 这的确有些道理 , 在苗寨中吃完一只鸡不吐骨头 , 没有人会对此感到讶异 。 可在别的文化里长大的人眼中 , 多少有些特别 。 2004年夏天我去韩国交流 , 檀国大学安教授陪同我去参观景福宫 , 中午安排在附近一家有名的高丽参鸡汤店用餐 , 落座后服务员摆上各种小碟开胃菜 , 之后就是主菜高丽参鸡汤 。 端上来两个木质托盘 , 每个托盘上放一口黑色砂锅 , 还沸腾不止的砂锅里是一只完整的鸡 , 安教授说是白凤鸡 。 鸡有一斤半大小 , 鸡腹内填塞有糯米和一根高丽参 。 稍降温后 , 我们拾筷开吃 。 由于鸡不大 , 炖得已经接近骨肉分离 , 我从头到身再到脚腿 , 不到半小时 , 整只鸡及汤饭已经见底 。 安教授望望我笑 , 我望望他笑 , 我只好解释说自己从小就吃饭速度有点快 。 他好奇问 , 是不好意思吐骨头吗?我解释说从小在家里养成了嚼碎骨头吞下的习惯 。 可当晚我的吃鸡之法成为了传说 。 当然 , 并非苗寨的人吃鸡不吐骨 , 只是本人自小养成嚼碎鸡骨鱼骨的吃法 , 吃高丽参鸡汤时不经意间被复制 , 从而让韩国朋友惊讶罢了 。 有一年台北辅仁大学的胡泽民教授同我去黔东南时 , 他用幽默的方式给我的嚼碎骨头之类的穷吃法提出了批评 , 他对当时在场的学生和教授们说 , 终于明白了苗族地区没有恐龙化石的原因 , 到苗族地区寻找化石是徒劳的 。
推荐阅读
- 咖啡店|咖啡店分三种:星巴克们、瑞幸们和即将死亡的小咖啡店
- 新世界|?“虎”形头枕、年货礼盒……南京路步行街“新年集市”带你提前过年
- 老抽|酱油、生抽、老抽和蚝油该怎么用?
- 植物肉|它被称为“植物肉”,几块钱做一盘,健脑补钙、好消化,一口能下3碗饭!
- 集市|虎元素、老字号还有进博同款,南京路上的新年集市带你提前过大年
- 菠菜|日本上班族推爆的居酒屋10大排行,鸟贵族、矶丸水产你爱哪一家?
- 面包|陈香味究竟是什么味?仓味、烟味、酸味是普洱老茶该有的味道吗?
- 春寿眉|从芽头、叶片到茶梗,教你分辨白牡丹饼与春寿眉饼,很全很详细
- 烧烤|这家大牌档扎根集美11年,开在学校边,每次集会都来这,海鲜、烧烤、川菜都有
- 挂面|同样是面条、买湿面好还是干面好告诉你区别,以后别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