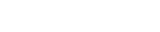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爸喜欢泡“酱油茶”, 所谓“酱油茶”, 是在偌小的一个小茶壶里塞满了茶叶, 然后加上滚烫的开水, 头几泡, 茶黑得可以当镜子, 故名“酱油茶” 。 我爸的特点是不来客人不泡这种“祖传秘茶”, 来越稀罕的客人, 酱油的浓度越高, 有时候, 高到了似油似酱的地步, 他要说明的无外乎有一点, 我们家舍得花大本钱请你茶, 你可一定要记住在我家的这一泡呀 。 我从来没象现在这么盼望家里来几个客人, 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从老家带回了一套茶具, 自从住到可亲可爱的大城市北京以后, 我已经越来越没有跟别人一起在家喝茶的经验, 要知道, 以前, 我们那里可是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家坐着胡扯 。 我们那里, 人们喝茶的场所在门外或者屋里的客厅, 门外喝茶的要么是家里的老人, 整日闲, 要么是看管店铺的商家, 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跟人谈价, 谈笑间, 该卖的都卖出去了, 买东西的人也觉得和气商量, 没有人把脖子弄粗嘴巴弄干, 其实店家一点都没吃亏, 作生意是要给生意人零头挣钱的 。 在客厅里喝茶通常是主客之间的一道社交课, 相反, 客厅的重要功能就是供一圈人坐着喝茶, 这样不至于太寂寞地把时间打发掉, 大家的语速保持着安稳, 主人在泡茶之前得把茶具用开水汤过一遍, 再把头遍茶水也倒掉, 最后才是喝真格的, 看他们操作, 近似于在一个小赌桌上, 给大家发牌, 客人的眼睛从进到客厅以后, 就跟着茶壶转, 你如果在我们镇呆久了, 会发现支撑大局的男人们表情很少, 他们不太会表达多于需要的感情, 要命的是语速特别慢, 连骂人都是慢悠悠地一个字一个字扔出来, 砸到人家头上, 这都是他们整天看泡茶看出来, 因为泡茶工夫外人看来虽然复杂, 如果每天都把一道复杂的程序重复十遍左右, 你就觉得太单调了, 甚至有点像一种陋习, 你如果习惯不了, 你就过不下去, 连泡茶都觉得累的人不是人 。 在大街上, 如果几个熟人见到, 往往说:“到家泡茶去 。 ”你可千万别真去, 他们还爱说另一句话:“到家吃饭去 。 ”那都不是发自内心地真请你吃饭, 只是一种招呼, 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说:“去我家把我的钱都拿走 。 ”那肯定不仅是客气, 那人八成有精神病, 龌县的人跟人还没好到共产共妻的程度 。 相比之下, 邀你泡茶是相对可信的, 不信你上门试试, 但到吃饭的点儿, 就该自觉地回家了 。 【在泡茶中永生】能喝茶的人跟爱抽烟的一样, 牙齿慢慢被染黄掉了, 你看到我们那里的男人, 不仅皮肤黑, 牙齿和手指头通常也是黑黄的, 这跟他们不怎么费劲就保持下来的生活方式有有很大的关系 。 茶垢是很厉害的, 通常一个新杯, 泡过一回茶后就开始起垢, 女人们的一个工作要点是保持家里茶具的干净, 但有些人专门把茶垢的印子留下来, 好说明他们从古早开始就喝茶, 这种传统在小脚时代就确立了, 比起日本的茶道, 讲道德讲礼貌讲排场的费劲, 我们那里的要实惠得多, 茶叶是便宜的到一盒三块的, 茶具是贱到一用八代的 。 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 不管在什么小馆子吃饭, 老板都会用一次性塑料杯给你上一口茶 。 一般茶的好坏不是入口的感觉, 而是它的样子, 如果是绿绿的立在水中, 都会迎来一片称赞 。 后来看了《胡雪岩》, 那时的人一早起来就去茶店, 在里面刷牙洗脸, 然后吩咐伙计打探各种消息(那时还没什么报纸), 很多人把茶店当作办公室, 有头面的人物一般还会有张专用大桌子 。 现在你常常能在北京上海广州之类的大城市看到南方茶馆, 那里边一泡茶都要上百块, 还按人头算水费, 也就是说, 你们三四个屁股占着三四个椅子都要算到茶钱里 。 那些穿着小蓝花花或小绿花花的衣服的姑娘, 按照某种经过长期培训的方法给你泡茶, 她们脸上浮现着一种跟文化无关的倦怠 。 如果茶馆上午关门了, 下午她们就可以换上红色小袄, 晚饭时给你端水煮鱼 。 我常常看着那些年轻俊俏的脸, 想起龌县特产黄脸婆, 我觉得同样是伺候人泡茶度日, 后者好歹算得上有那么点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