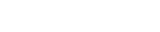喝茶是一门学问 。 所以日本有了茶道 。 据说茶叶和佛教一样 , 是由中国大际传往岛国的 , 日本人把两者包容了 , 在喝茶的礼仪中也讲究禅境与悟性 , 沏一道茶时的思辩或修养不亚于吾乡人操持满汉全席般隆重 。 现在 , 是中国人颠倒过来要向日本人打听及学习茶道了 。 茶道仿佛也像原装松下电器似的 。 成为舶来品--大和民族真是联盟也很怪异 。 关于茶道 , 周作人如此解释:“茶道的意思 , 用平凡的话来说 , 可以称作‘忙里偷亲、苦中作乐’ , 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与和谐 。 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 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 ”世界是不完善的 , 人终须凭借某些手段获得完美的错觉 , 茶道恰是手段之一 。 周作人把茶道讲授得很清白 , 但他本身是历史上较复杂的人物 。 他解放前在北平八道湾有一套书房 , 原名苦雨斋 , 后改为苦茶庵了 。 究竟为何易名 , 他深缄其口 , 讳莫如深 。 或许表明雨是天降的 , 而茶是人为的--天意与人事的变更?据说室内挂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条幅 , 刻意追求一份行到水穷处 , 坐看去起时的境界 。 半个世纪过云了 , 坐落于老城拆迁区的所谓苦茶庵该已沦为一片废墟了吧?我总听见岁月的影壁后面传来一个老人沙哑的嗓音:“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 , 清泉绿茶 , 用素雅的陶瓷茶具 , 同二三人共饮 , 得半日之闲 , 可抵十年的尘梦 。 喝茶之后 , 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 , 无论为名为利 , 都无不可 , 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 。 ”看来 , 茶道并非教诲人们饮水思源 , 或一劳永逸地坐忘尘世 , 不过给人们追名逐利之余提供一番小憩罢了 。
十年以前 , 百姓路吉作人的 , 比知道鲁迅的少得多 。 同样 , 周作人的苦茶庵 , 怕只在知识阶层有所流传 , 而说起老舍的茶馆 , 国人几乎无不晓 。 那已是一座超现实的茶馆 , 云集旧时代的三都九流 , 有提笼遛鸟的遗老遗少 , 也有说书的江湖艺人、卖唱的天涯歌女乃至歇脚打尖的人力车夫……纸上的茶馆 , 因网罗了栩栩如生的众生相而风吹不倒 。 苦茶庵是个人主义的 , 而老舍笔下平民化的北京茶馆则弃雅就俗 , 返璞归真 。 老舍而骄傲--就像巴黎的回顾展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 老舍生前肯定没开过茶馆 , 没当过掌柜 。 但在他死后 , 在正阳门一带 , 确实有一座老舍茶馆平地而起 。 据说里面也安排拉二胡的、唱戏的 , 但店面封资修得过于豪华 。 连招牌都烫金的--我上下班骑车 , 总过其门而不入 。 我是怕自己失望 。 那里面肯定没五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卖了 。 那里面更找不到骆驼祥子的影子了 。 老舍寂寞的时候 , 会来这喝茶吗?后来我学会安慰自己:忽略安深厚的商业色彩吧 , 就把它当作老舍的纪念馆 , 纪念一位仍然在北京城的记忆中活着的死者……
【北 京 茶 话】老舍茶馆是北京的专利 。 在南方 , 阳澄湖一带 , 人们议论着阿庆嫂的春来茶馆--它同样是地图上找不到的 。 春来茶馆是因现代京剧《沙家浜》而出名的 。 《沙家浜》的作者是汪曾祺 。 “祭起七星灶 , 铜壶煮三江 。 来的都是客 , 全凭嘴一张……”我逛街常听见有人哼这段子 , 或放这磁带 。 也许他们不知道汪曾祺是谁 。 但他们明明在唱汪曾祺写的歌词 。 这就可以了 。 记得那回我见汪先生 , 很激动 , 耳朵里尽回响着阿庆嫂的唱腔 。 汪先生也是文坛上有名的茶客 , 写过一篇《泡茶馆》 , 完全凭记忆追怀搞战期间西南联大校门口的一系列茶馆 , 及其布置风格的区别 。 他以深深的感激作为结尾:“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 , 我对各种各样的人 , 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 , 都想了解了解 , 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 。 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 , 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 ”昆明的茶馆是有福的 , 它泡出了一位小说家 。
推荐阅读
- 茶 具 文 化
- 白兰花茶
- 微波技术在制茶业中的应用
- 菊花茶|菊花茶的栽培种植技术
- 秋季茶树茶园管理:茶叶栽培技术与管理措施
- 无公害食品 茶叶产地环境条件
- 潮人饮茶礼俗
- 易贡茶
- 奥兰多的茶文化
- 茶的泡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