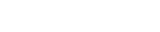包慧怡
手抄与印刷
陆大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世纪没有对原创性的迷思,主要和介质昂贵有关?当印刷术开始普及,可以比较便宜地大规模复制书籍,原创性就越来越受重视?
包慧怡: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三十年,英国商人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伦敦成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 。他当时选择付梓的文本也是精挑细选后决定的:一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是托马斯·马洛里(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85) 。卡克斯顿四处漫游,他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书,他选择印这两位生平可考的作者的作品,把写作从混沌当中打捞出来,让人们终于可以讨论单数的作者 。而乔叟可以成为英国文学之父,也与他的书被印得多、读者多有关 。但这一切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比如位于西方正典核心的莎士比亚也没有对署名的执着,他仅在诗集上署名,他的剧本在生前从没出版过,甚至他留下的三十几个签名里,每个拼写都不一样,因为那时没有正字法 。
蔡伟杰:在清史研究中,面对满、蒙、藏文的档案,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翻译 。可以说,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翻译已经和研究结合在了一起 。我也不觉得翻译工作本身更容易,它需要译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理解作者和相关的时代 。比如我译《中国西征》时,需要核查大量引文,有时候发现作者的理解有误,我再出个注,标明这个地方的原文实际是什么,英译文是什么样的,英文的误译如何导致了作者错误的理解 。某种程度上,翻译也是再创作的过程,是译者和作者对话的结果,因此翻译作品也有自己的生命 。
陆大鹏:我前段时间在一个英文播客里听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哀叹,生活在数字时代的学生,从小读印刷品或电子书长大,以至于如今历史学面临的一大障碍便是,能阅读手写体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到对新发现的南北战争时期李将军的书信都识读不了的地步 。两位老师都有阅读古代手写体资料的经验,你们觉得识读困难吗?
陆大鹏
包慧怡:我无法想象南北战争时期的文本就已经读不了了,我想李将军的字还不至于草成那样 。在中世纪文本领域,古文书学(paleography)是一门单独的学科 。中世纪有一套完整的缩写系统,当时的一些字体,比如哥特黑体,尽管方方正正,易于辨识,但有的人在书写时喜欢炫技连写,让人读起来犹如猜谜,这就给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做研究,如果没有印刷的精校本,就要先花大量时间从羊皮转写(transliteration),自己生成文本 。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是十足的体力活,通常一天能转写半页到一页就很不错了,有时甚至要训练自己对字体产生肌肉记忆 。而哥特黑体已经算比较规律的字体了,更难认的还有私生子体、岛屿大斜体、加洛林王朝小写体……我们把挤在一起的字母称为“字母汤”(alphabet soup),类似字母大乱炖,它们让整个识别过程好像破案 。在拉丁文或古英文转写完后,第二步是把它们翻译成现代语言,到第三步研究才开始 。当然,我们研究的大部分内容都有精校本,也就是说我们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工作的 。一般情况下,即便要转录,你也不会转写整个抄本,而只是摘取其中对研究有价值的部分 。
推荐阅读
- tcl是国企吗,盘点国企四大巨头
- 转氨酶升高就是肝病? 转氨酶偏高
- hdr下载后就是JPG解释 hdr下载后就是JPG
- UK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英国简称吗 uk的全称是什么
- 100元学平险都保什么 学平险是什么
- 合欢耐寒吗
- 姐姐就是玩儿是哪个歌 姐姐歌词
- 档案管理系统操作步骤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软件排名
- 如何预约上海博物馆门票 上海博物馆开放时间
- 魏晋时期有多开放 魏晋南北朝荒唐又美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