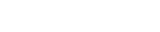看到它的第一眼 , 霎时许多理由都鱼贯而出:不锈钢杯装水有铁锈味;塑料杯除了塑料味之外还有一种应付的气味;那只特价瓷杯没盖 , 跑气;也许不能因为它有深浅不一的青色就叫它青花瓷杯 , 极有可能这只是一种装饰的颜色而不是工艺 。 缘于我喜欢青花二字 , 觉得这样叫一个瓷器能把瓷器叫老 , 而把人则叫回简单纯粹 。 它呆在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货架上 。 也许洁白通透才是瓷器的最佳形态 , 货架上简洁居多 , 这个通身是深深浅浅繁复的花的瓷杯 , 如一个滚得浑身是泥的乡里孩子初次走上街头 , 纯朴拘束 。 丢几片茶叶进去 。 茶叶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 二十元一斤 , 装在大大小小的竹箩筐摆在巷底 , 巷子叫茶巷子 , 是否因卖茶叶为多 , 不得而知 。 喝完再买 , 一壶永远在烧的水倒入玻璃杯里 , 走两步到巷中 , 对着太阳看颜色与浮沉 。 好的 , 拿一斤 , 分两个袋子装 。 【一只青花瓷杯】总觉得茶叶最好用瓷器泡 , 特别是绿茶 , 铁杯与塑料杯根本就是糟蹋茶 , 就算是八元一斤的粗茶 , 用碗喝也好过这些 , 玻璃杯亦有一种细微的玻璃气息 , 易传热 , 初时不能捧 , 待能捧时不一会就感觉温度嗖跟地从指间滑逸 。 玻璃透明 , 一杯茶从浮到沉 , 从炽热到冰凉 , 从远及近 , 了然于胸 。 瓷杯如谦谦君子 , 从不把它的味道窜出来 , 又最好握 , 沉稳的热徐徐地传入手心 , 能一直温到茶尽 , 又往往给人隐匿的愉悦 , 挡住视线 , 你不知它里面与背后藏着些什么 , 你必须伸过眼去看它 。 关于瓷器的伸过眼 , 最记得儿时 , 吃饭装菜用的是极粗糙的碗 , 麻点不必说 , 一枝红梅伸着伸着花色突然就断了的亦是常事 , 甚至碗口都不够圆 。 艰苦让这些也堂皇的成为了财产的一部份 , 乡里邻里吃饭喜欢窜门 , 或者互赠好菜 , 饭菜碗混淆是常有的事 。 为了区别 , 各家就在碗上钉字 , 字一般是儿女的名字 , 这样也就标明财产所属了 , 两个小兄弟闹意见了 , 哥哥是决计不让弟弟拿他的碗 , 满禾场追着跑 , 弟弟跑不赢 , 把碗撒手一丢 , 禾场地软 , 碗又粗厚 , 摔不破 , 滚几滚 , 引来凑着鼻子的狗 。 舅舅家儿女众多 , 碗底有字:来 , 良 , 军 , 辉 , 桃 。 字应是拿细尖细尖的东西戳出来的 , 只把釉面戳掉 , 露出细细点点的黄褐色的底里 。 不过那个黄褐色现在想来应是经年的菜汤浸染所至 , 再粗的瓷也应是白色才对 。 来是老大 , 儿子 , 又有出息 。 所以舅舅家“来”字的碗最多 , 混到我家的也就多了 , 有时吃着吃着菜 , 两根湿搭搭的红菜苔下面 , 俨然有字 , 我与姐就打堵 , 看是哪个字 , 猜中了的 , 那剩下的两根菜就是赌品 。 舅妈一到我家来就到碗柜里看 , 说你看你看 , 这是我们家的碗 , 又跑到你家来了 。 我抢嘴道:是你上次端菜来 , 又忘了拿走 , 再说我屋的碗不知有多少有你家里呢 , 我家的碗还比你家贵呢 。 妈在一旁 , 那气的情形 , 像要马上跳起来打我 。 打还是没打 , 记不清了 , 我想应是打过的 。 现用的瓷器 , 除了碗 , 就是茶杯 。 其它的用具早就被其它的东西代替 , 我记得那时家里有许多瓷器用具 , 糖油黄豆碗豆都用瓷罐 , 靛蓝花色 , 厚重质朴 。 表嫂家的一双儿女好吃 , 表嫂就把有些瓷罐藏在衣柜里 。 没想她儿子晚上起夜 , 竟打开柜门打开罐口径直朝里射 , 第二日表姐闻到异味 , 才发现一罐黄豆与碗豆都泡软了 , 目标非常准确 , 旁边的衣服却未沾染 , 更怪的是 , 儿子竟然毫无记忆 , 朝死里打也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 直到一天晚上当场逮到儿子起夜 , 他正准备伸手打开衣柜 , 充耳不闻呵斥的样子 , 灯打开时发现孩子在梦游 。 后来是怎样把梦游成功地牵引到厕所 , 忘记打听了 。 一些字下来 , 茶已凉了 , 二十元一斤的茶叶果然不见有多好 , 一凉就苦 , 发涩 。 不过这种茶从小喝起 , 苦涩也成了习惯 , 习惯把最后的凉茶一仰脖灌下去了事 , 溜进几片茶叶也一并嚼了 。 这只我所谓的青花瓷杯 , 完成了今天最后一泡茶的任务 , 静静地坐在灯下 , 通体繁杂热闹的花在瓷的质地下出奇的沉静洁雅 , 宛若最癫狂绚烂的爱情 , 被时间沉淀成无语的生命搀扶 。
推荐阅读
- 在秋天的青花茶碗里
- 炒青花菜的家常做法 素炒西兰花的做法大全
- 每日一只庄家出货的股票分析宏盛股份603090
- 每日一只庄家出货的股票分析603613国联股份
- 每日一只庄家出货的股票分析天宇股份300702
- 每日一禅:佛塔里的老鼠
- 用陶瓷笔画一只食物碗 随时掌握猫咪小心情!
- A股下一只贵州茅台可能会在什么领域产生?
- 做一只可爱的豆糕蛙 橡皮泥制作小青蛙图解
- 青花风格零钱包/收纳包手工制作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