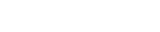дёҖзүҮз№ҒиЎҚеҚғе№ҙзҡ„дёҮдә©еҸӨиҢ¶еӣӯпјҢ еҲҶеёғзқҖжҷҜиҝҲгҖҒиҠ’жҷҜгҖҒиҠ’жҙӘгҖҒеӢҗжң¬гҖҒзҝҒеұ…гҖҒзҝҒжҙјзӯүеҸӨиҖҒзҡ„жқ‘еҜЁпјҢ зҲ¬ж»Ўйқ’иӢ”зҡ„еҸӨиҢ¶ж ‘е°ұз”ҹй•ҝеңЁжқ‘еүҚеұӢеҗҺпјҢ е№ҙе№ҙзӯүжҳҘжқҘпјҢ еІҒеІҒеҗҗж–°иҠҪ гҖӮ дёҖж–№ж–‘й©ізҡ„зҹізў‘дёҠйӣ•еҲ»зқҖжё…жҷ°зҡ„еӮЈж–ҮпјҢ и®°еҪ•дёӢиҠ’жҷҜиҢ¶еҸ¶з§ҚжӨҚе§ӢдәҺеӮЈеҺҶ57е№ҙ(е…¬е…ғ695е№ҙ)пјҢ и·қд»Ҡе·Іжңүиҝ‘1300е№ҙзҡ„еҺҶеҸІ гҖӮ дёҖжҲ·жҲ·д»ҘиҢ¶дёәз”ҹзҡ„еӮЈе®¶дәәгҖҒеёғжң—дәәпјҢ жҳҘйҮҮз§Ӣ收пјҢ е©ҙе„ҝдјҙзқҖиҢ¶йҰҷиҗҪең°пјҢ еҶҚеӨ§дәӣж—¶е°ұжҠҠеңҶжәңжәңзҡ„иҢ¶жһңеҪ“жҲҗзҺ©е…·пјӣзј зқҖеёғеҢ…еӨҙзҡ„иҖҒдәәеңЁзҒ«еЎҳиҫ№еҗёзқҖж°ҙзғҹзӯ’пјҢ з”Ёй“ңеЈ¶з…®ејҖдёҖеЈ¶еӨҙе№ҙзҡ„иҖҒй»„зүҮ гҖӮ иҸ©жҸҗж ‘дёӢзҡ„жё…жҷЁ е°Ҫз®Ўеӣ°еҫ—зқҒдёҚејҖзңјпјҢ жҲ‘иҝҳжҳҜдёҚжғій”ҷиҝҮжқҘжҷҜиҝҲзҡ„第дёҖдёӘжё…жҷЁ гҖӮ жё…жҷЁ7зӮ№дёҚеҲ°пјҢ жҘјжқҝдёӢзҡ„зүӣй“ғе“ҚдәҶиө·жқҘпјҢ ж•ҙеӨңйҮҢжӮ„з„¶ж— еЈ°зҡ„йӮЈзҫӨзүӣе„ҝжҷғзқҖй“ңй“ғй“ӣеҮәй—ЁдәҶпјҢ жңҰиғ§дёӯеҗ¬и§ҒеІ©жё©зҡ„жҜҚдәІејҖе§ӢеңЁзҒ«еЎҳиҫ№еҝҷзўҢ гҖӮ еқҗиө·иә«жқҘпјҢ жүҚеҸ‘зҺ°еҗҲиЎЈиҖҢеҚ§зҡ„еҘҪеӨ„е°ұжҳҜиө·еәҠе®һеңЁеҲ©зҙў гҖӮ й’»еҮәжңЁжқҝжҲҝпјҢ е№іеҸ°еӨ–дә‘йӣҫйҒ®дҪҸдәҶеӨ§еҚҠдёӘжқ‘еә„пјҢ й«ҳеӨ„зҡ„жңЁжҘјйЎ¶еҒ¶е°”еңЁеӨ§йӣҫйҮҢйңІеҮәж°ҙзүӣи§’иҲ¬зҡ„зҝҳи§’пјҢ зј…еҜәйҮ‘иүІдҪӣеЎ”зҡ„еЎ”е°–йЈҳжө®еңЁдә‘жө·д№ӢдёҠпјҢ еӨӘйҳіжңӘи§ҒиёӘеҪұпјҢ з©әж°”жҪ®ж№ҝеҶ·еҶҪ гҖӮ дёӢдәҶжңЁжҘјжүҚеҸ‘зҺ°иҚүеҸ¶е’Ңең°йқўйғҪжҳҜж№ҝжјүжјүзҡ„пјҢ зј…еҜәзҡ„еӨ§й—Ёж—©е·Іж•һејҖпјҢ зҷҪеҸ‘зәўиўҚзҡ„иҖҒдҪӣзҲ·еңЁдҪӣеҸ°еүҚжҚўдёҠдёҖзў—дҫӣеҘүзҡ„жё…ж°ҙ гҖӮ дёҖдҪҚеӮЈж—ҸиҖҒдәәеҲҷеңЁзј…еҜәеӣӣи§’зҡ„жңЁжҹұеӨҙеҗ„зӮ№дёҠдёҖж”Ҝз»Ҷз»Ҷзҡ„иңЎзғӣпјҢ жҸҗзқҖиҢ¶еЈ¶еңЁжҜҸдёӘжңЁжҹұзҡ„еӣӣе‘Ёж’’дёӢеҮ ж»ҙиҢ¶ж°ҙ гҖӮ еҜәеҗҺжңүжЈөй«ҳеӨ§зҡ„иҸ©жҸҗж ‘жһқеҸ¶йқ’иҢӮдҫқж—§пјҢ дёҖзүҮзүҮеҝғеһӢзҡ„иҸ©жҸҗеҸ¶е№¶жІЎеӣ з§ӢеҜ’иҖҢжһҜй»„пјҢ еҚҺзӣ–иҲ¬зҡ„ж ‘еҶ еҮ д№ҺйҒ®дҪҸдәҶеҚҠдёӘеӨ©дә• гҖӮ зј…еҜәйҮҢзҡ„иҸ©иҗЁеҗҲзӣ®жҠҠеҫ®з¬‘йҖҸиҝҮиҸ©жҸҗеҚҺжһқпјҢ жҠӨдҪ‘зқҖеұұйҮҺе’Ңжқ‘еә„ гҖӮ еӣһеҲ°еұӢйҮҢпјҢ еІ©жё©зҡ„жҜҚдәІж—©з…®еҘҪдәҶйҘӯпјҢ 家йҮҢдәәеҗ„иҮӘеҢ…дәҶдёҖиўӢе°ұеҮәй—ЁйҮҮиҢ¶зҡ„йҮҮиҢ¶пјҢ 收йәҰеӯҗзҡ„收йәҰеӯҗеҺ»дәҶ гҖӮ зҒ«еЎҳиҫ№е°ұз•ҷдёӢдәҶжҲ‘们иҮӘе·ұ гҖӮ иө¶еҝ«еҗғиҝҮж—©йӨҗпјҢ еҶҚеҮәй—Ёж—¶пјҢ ж—Ҙе·Ій«ҳеҚҮпјҢ еӢҗжң¬жқ‘家家жҲ·жҲ·зҡ„жңЁжҘјйғҪжҡ–жҡ–ең°иһҚеңЁз§ӢйҳійҮҢпјҢ йҮ‘иүІдҪӣеЎ”еңЁзҷҪиүІдә‘жө·й—ҙиҖҖзңјеҰӮд»ҷеўғ гҖӮ ж»Ўжқ‘е°Ҫжҹ“еҸӨиҢ¶йҰҷ жӯЈеҚҲпјҢ еӨ§йӣҫж•Је°ҪпјҢ йҳіе…үжҠҠзј…еҜәзҡ„йҮ‘иүІдҪӣеЎ”жҳ з…§еҫ—зҒҝзғӮдёҚе·І гҖӮ еӢҗжң¬жқ‘зҡ„жқ‘ж°‘еңЁе®¶й—ЁеҸЈе’Ңе№іеҸ°дёҠж‘ҠејҖдёҖеј еј з«№еёӯпјҢ жҸүжҚ»еҘҪзҡ„иҢ¶еҸ¶иЈ…еңЁиғҢзҜ“йҮҢпјҢ е®Ңж•ҙеЈ®е®һзҡ„жқЎзҙўжҹ”иҪҜең°еҚ·жӣІзқҖпјҢ йқ’з»ҝеҸҜзҲұпјҢ з”ЁжүӢж‘ёж‘ёпјҢ ж„ҹи§үзІҳзІҳзҡ„пјҢ ж»ЎжҳҜжҸүеҲ¶еҗҺ涔еҮәзҡ„иҢ¶жұҒпјҢ еӯҰзқҖжқ‘ж°‘ж ·жҲ‘们дёҖжҠҠжҠҠе°Ҷе®ғ们еқҮеҢҖең°ж‘Ҡж’’еңЁз«№еёӯдёҠжҷҫжҷ’ гҖӮ еҮ дёӘе°Ҹж—¶еҗҺпјҢ дәә们иҝҳиҰҒжҠҠејҖе§Ӣе№ІзҮҘзҡ„жҜӣиҢ¶йҮҚж–°зҝ»жҷ’дёҖйҒҚпјҢ и®©еҸ¶зүҮзҡ„жҜҸдёӘйқўйғҪйҘұеҗёеҲ°еӨӘйҳізҡ„зғӯеәҰиҖҢе№ІзҮҘеҫ—жӣҙеҪ»еә•пјҢ еӢҗжң¬жқ‘ж№ҝж¶Ұзҡ„з©әж°”йҮҢе……ж»ЎдәҶд»ӨдәәжІүйҶүзҡ„иҢ¶еҸ¶жё…йҰҷ гҖӮ дёҖдәӣдәҢдёүзұій«ҳзҡ„еҸӨиҢ¶ж ‘йҡҸж„Ҹж•ЈиҗҪеңЁжқ‘民家зҡ„еұӢеүҚеұӢеҗҺпјҢ дёҖжЈөиҝ‘дёүзұій«ҳзҡ„иҢ¶ж ‘пјҢ д»ҺдёҖжҲ·дәә家еӣҙйҷўзҡ„зҹіеўҷйҮҢдјёеҮәжқҘпјҢ е°Ҹеңҹзў—зІ—зҡ„ж ‘е№ІпјҢ еҸ¶зүҮжІ№дә®пјҢ дёҚзҹҘйҒ“жҳҜе…Ҳжңүж ‘иҝҳжҳҜе…Ҳжңүеўҷ гҖӮ жқ‘ж°‘й—ЁиҜҙиҝҷдәӣиҢ¶ж ‘д№ҹдёҚзҹҘжҳҜд»Һд»Җд№Ҳж—¶еҖҷе°ұжңүзҡ„пјҢ жҲ–иҖ…他们е°ұе№Іи„ҶиҜҙпјҡиҝҷжҳҜеӯ”жҳҺз•ҷдёӢжқҘзҡ„ гҖӮ еёҰзқҖиҝ‘и§Ҷзңјй•ңзҡ„еІ©зҪ•зҸҚжҳҜеӢҗжң¬жқ‘зҡ„еҢ»з”ҹпјҢ д№ҹжҳҜжқ‘йҮҢжңүеӯҰй—®еҲ°иҝҮзңҒеҹҺжҳҶжҳҺзҡ„е№ҙиҪ»дәәпјҢ д»–еңЁжқ‘еқЎеӨҙејҖдәҶй—ҙз®ҖеҚ•зҡ„е°ҸиҜҠжүҖпјҢ дёӨе№ҙеүҚд№ҹжҲҗз«ӢдәҶеҠ е·ҘеҺӮ收иҢ¶еҒҡиҢ¶ гҖӮ еӨӘйҳіиҗҪеұұж—¶жҲ‘们жқҘеҲ°еІ©зҪ•зҸҚ家пјҢ 他家еҗҺйқўжҳҜй•ҝж»ЎиҢ¶ж ‘зҡ„зј“еқЎпјҢ еүҚйқўеҲҷжҳҜеҲҖеүҠиҲ¬зҡ„йҷЎеқЎпјҢ еӨӘйҳіжӯЈеҘҪд»ҺйҷЎеқЎйӮЈеӨҙиҗҪдёӢеҺ»пјҢ й—ЁеҸЈе№іең°дёҠж‘ҶдәҶеј еӣӣж–№жңЁжЎҢпјҢ еІ©зҪ•зҸҚзҡ„е…„ејҹзҷҪеӨ©еңЁж°ҙиҫ№жҠ“йұјж—¶йЎәдҫҝж‘ҳжқҘдёҖеӨ§и“¬йҮҺиҸңпјҢ з”Ёе°ҸзұіиҫЈе’Ңе§ңиұҶйј“и°ғдәҶдёҖеӨ§зў—иҳёж°ҙпјҢ е°ұиҝҷж ·з”ҹиҳёзқҖеҗғ гҖӮ йҮҺиҸңжңүиӮЎиүҫиҚүиҲ¬зҡ„йҰҷе‘іпјҢ й…ҚзқҖе’ёиҫЈзҲҪеҸЈзҡ„иҳёж°ҙзү№еҲ«ејҖиғғпјҢ иҝһе№іж—ҘйҘӯйҮҸдёҚеӨ§зҡ„жҲ‘йғҪиҝһеҗғдәҶдёӨеңҹзў—зұійҘӯ гҖӮ еІ©дҫқеӢҮеӨңжқҘж‘ҶеҸӨ йҘӯжҜ•пјҢ еңЁжҳҸй»„зҡ„зҒҜе…үдёӢдёҖзҫӨдәәеӣҙеқҗиҜ•жіЎзҷҪеӨ©еҲҡеҒҡеҘҪзҡ„з§ӢиҢ¶ гҖӮ еІ©зҪ•зҸҚзҡ„зҲ¶дәІеІ©дҫқеӢҮжҳҜжҷҜиҝҲжқ‘еҺҹжқҘзҡ„иҖҒж”Ҝд№ҰпјҢ 53еІҒзҡ„еІ©дҫқеӢҮдёҚеғҸжҲ‘们用е°ҸзҺ»з’ғжқҜзӯүзқҖе…¬йҒ“жқҜйҮҢзҡ„иҢ¶жұӨпјҢ д»–жӣҙе–ңж¬ўз”ЁеӨ§жҗӘз“·еҸЈзјёжіЎдёҖжқҜжө“жө“зҡ„иҖҒй»„зүҮпјҢ иҫ№е–қиҫ№е’•еҷңе’•еҷңең°жҠҪзқҖж°ҙзғҹзӯ’ гҖӮ еҒҘи°Ҳзҡ„еІ©дҫқеӢҮеҜ№жҷҜиҝҲзҡ„жҺҢж•…еҰӮ数家зҸҚ,д»–иҜҙеҺҶеҸІдёҠжҷҜиҝҲ8дёӘжқ‘зҡ„иҖҒзҷҫ姓е°ұжңүйҮҮж‘ҳжҷҜиҝҲеҸӨиҢ¶зҡ„д№ жғҜпјҢ е°Ҹж—¶еҖҷиҝҳи§ҒиҝҮиҮӘе·ұзҡ„еҘ¶еҘ¶иғҢиҢ¶еҺ»еҚ– гҖӮ еҪ“ж—¶зҡ„дәә们用з¬ӢеҸ¶е’Ңз«№зҜ®жқҘеҢ…иЈ…жҜӣиҢ¶пјҢ дёҖйғЁеҲҶиҢ¶з”ЁдәәиғҢ马驮пјҢ еҲ°жҷ®жҙұиҝӣиЎҢдәӨжҳ“дҪңдёәжҷ®жҙұиҢ¶зҡ„еҺҹж–ҷ гҖӮ еҸҰдёҖйғЁеҲҶиҢ¶еҲҷзӣҙжҺҘйҖҡиҝҮдёӯзј…иҫ№еўғзҡ„жҙӣеӢҗе’Ңжү“жҙӣпјҢ иҝӣе…Ҙзј…з”ёпјҢ еҶҚй”ҖеҲ°дёңеҚ—дәҡеҗ„еӣҪ гҖӮ д»ҘеүҚиҝҷйҮҢзҡ„еӨҡж•°иҢ¶ж ‘дёҠйғҪй•ҝзқҖвҖңиһғиҹ№и„ҡвҖқе’Ңеҗ„з§Қеҗ„ж ·зҡ„еҜ„з”ҹзү©пјҢ жңҖеҲқдәә们жҠҠвҖңиһғиҹ№и„ҡвҖқжүҜдёӢжқҘе–ӮзүӣпјҢ еҗҺжқҘеҚ–еҮәеҺ»зҡ„иҢ¶еҸ¶дёӯеҒ¶е°”ж··дәҶдәӣиҝӣеҺ»пјҢ иў«еӨ–йқўзҡ„дәәи®ӨдёәжҳҜеҘҪдёңиҘҝпјҢ иҝҳжҠҠжңүвҖңиһғиҹ№и„ҡвҖқеҒҡдёәжҷҜиҝҲиҢ¶зҡ„ж Үеҝ— гҖӮ зҺ°еңЁжҷҜиҝҲзү№жңүзҡ„вҖңиһғиҹ№и„ҡвҖқеӣ д»·ж јй«ҳйҮҮж‘ҳиҝҮеәҰиҖҢи¶ҠжқҘи¶ҠзЁҖе°‘пјҢ иҢ¶еҶң们ејҖзҺ©з¬‘иҜҙпјҢ йҮҮвҖңиһғиҹ№и„ҡвҖқиҰҒзңӢиҝҗж°”е‘ў гҖӮ иҒҠеҲ°иө·жҷҜиҝҲеҸӨиҢ¶ж ‘пјҢ иҜҙеҲ°еҪ“е№ҙжҖқиҢ…ең°еҢәдё»з®ЎиҢ¶еҸ¶зҡ„еӨ–иҙёеұҖеүҜеұҖй•ҝдҪ•д»•еҚҺе…Ҳз”ҹеҲ°жҷҜиҝҲдҝқжҠӨеҸӨиҢ¶ж ‘зҡ„еҫҖдәӢпјҢ еІ©дҫқеӢҮжҝҖеҠЁең°иҜҙпјҡеҪ“ж—¶еёҰдҪ•иҖҒиҝӣеұұзҡ„е°ұжҳҜжҲ‘е•ҠпјҒ гҖҗеӢҗжң¬зҡ„жҷЁ?еҚҲ?еӨңгҖ‘
жҺЁиҚҗйҳ…иҜ»
- зҺ°д»Јдәәе“ҒиҢ¶зҡ„дёғз§ҚзҗҶз”ұ
- ж•ҷдҪ е·§ејҖиҢ¶еҸ¶еә—
- е“Әз§ҚиҝҗеҠЁжңҖеҮҸиӮҘпјҹ
- е‘Ёиҫ№ең°еҢәе»әи®ҫ银иЎҢиҗҘдёҡзҪ‘зӮ№дёҺATMжңәзҡ„жҹҘиҜўж–№жі•
- жҖҺж ·дҪҝжңүиүІиЎЈжңҚдёҚиӨӘиүІ
- ејҖдёҖдёӘиөҡй’ұзҡ„ж°ҙжһңеә—
- 5Gе’Ң4Gзҡ„еҢәеҲ«жҳҜд»Җд№Ҳ
- еҺ»йҹ©еӣҪж•ҙеҪўеҸҜд»ҘйҖҖзЁҺеҗ—
- дә‘еҚ—иҢ¶дҪ зҡ„еҗҚеӯ—еә”иҜҘе…Ёдё–з•ҢйғҪзҹҘйҒ“пјҢзҷҪиҢ¶зҡ„з§Қзұ»
- е°ҙе°¬зҡ„еҗҚиҢ¶ вҖңд№Ңзүӣж—©вҖқзҡ„еҮәи·ҜеңЁе“ӘйҮҢпјҹпјҢжЎӮиҠұи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