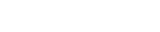这是最后的日子了 , 我们请求母亲必然来陪护:一是病情越来越重 , 父亲需要时刻有人在身边 , 我得跑上跑下 , 踏出病房一步都难以安心;二是我那时正在重伤风 , 父亲已经几乎没有免疫力了 , 我一个喷嚏 , 对他来说即是落井下石 。 最主要的是 , 在父亲最后的旅程里 , 我们作为后代始终无法取代母亲的位置 , 我们也不但愿母亲日后有遗憾 。
母亲终于肯到病院了 。 日夜守着丈夫 , 给他擦身洗脸、按摩捶背 。 到了饭点叫她吃饭 , 她说不饿;叫她歇息 , 她说不困 。 只是 , 一旦我偶然有事外出 , 父亲呈现告急状况 , 母亲第一时候想到的不是找大夫护士 , 或者给我德律风 , 而是打德律风去找算卦师长教师 。 那段时候 , 爸妈面临彼此的时辰 , 经常陷入缄默且尴尬的状况——尽管到了生命的最后 , 他们也没能敞高兴扉说说心底话 。
“有神明保佑 , 你必然不会有事的 。 ”这是母亲长久以来对父亲所说的独一的抚慰 。
父亲又一次盆腔出血 , 麻醉师赶来给他插深静脉置管 。 母亲站在门口望着 , 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哽咽:“我仍是不克不及接管啊 , 我从来不敢去找大夫 , 我怕知道你爸的环境 , 怕他再也好不起来……”
但父亲仍是走到了最后一程 。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 移植大夫、科室本家儿任、资深病友都摇头感喟 。 如斯 , 能让父亲顺遂回到老家就是我们最后的但愿了 。
7 月 1 日打点出院 , 回到老家将父亲安放好后 , 母亲害怕日后睹物思人 , 连夜赶往小镇、县城的家 , 将父亲所有的衣物、药品等打包好 , 筹办拿去扔了作罢 。
父亲用不上的药还剩十几种 , 此中包罗一盒尚未拆封的乐伐替尼(上万元)、一瓶几百块的白卵白 , 我和母亲筹议:“既然这些药咱们用不上 , 不如给那些等着救命的病友?”
“不可 , 没用了就十足拿去扔失落!”
我领会母亲的性格 , 只好假装应下 , 趁她不注重 , 暗暗把两大袋药拎落发门 , 藏到了奶奶的柴垛里 。 可最终我的小心思仍是没能躲过母亲的眼睛 。
“你把药拿去哪里了?快交出来!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聊 , 快快拿出来!”
“不给!”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掷地有声地与母亲抗衡 。
我理解母亲 , 也许在她看来 , 将残剩的药丢弃 , 家里就能从此隔离了病根 。
可我心里还想着那些吃不起正版靶标的目的药、但为了活命不得不经由过程不法路子吃原料药的战友们 , 想起这么长时候、和我与父亲同在抗癌路上茫然无措时互帮合作的病友们 , 想起那些捐募器官的好心人 , 想起父亲一辈子与报酬善 , 又怎么忍心看这些救命药沦为垃圾堆里的灰烬呢?
我仍是暗暗把这些药寄了出去 。
回到老家后的父亲吐得更厉害了 , 大小便也掉禁了 。 7 月 6 日早晨 , 我在厨房做早饭 , 父亲对母亲说 , 他想去处所病院插下尿管 。
“不消去了 , 没用的 。 你有什么要交接的就快说吧 , 否则就得本身闷在心里了……”母亲曾经那么坚信父亲会有好起来的一天 , 现在却又亲自砍断了他的最后一丝但愿 。
在母亲的训斥下 , 我去小镇买处置后事用品 。 那一天 , 狠毒的日头炙烤着村庄 , 一片死寂 , 那没等我归去 , 父亲便与我不辞而别 。 “快哭啊!高声哭啊!”当我飞驰抵家时 , 母亲在一旁催促 。
我跪在地上 , 双手合十 , 双腿瘫软 。 母亲还在一向教我应该怎么哭 , 但我却始终哭不作声来 。 我只知道 , 他再也不会像个孩子一样 , 委屈地跟我说这里痛、那边不舒畅 , 再也不消熬着吃药比吃饭多的辛酸日子 , 他终于分开了这个熬煎他的人世 。
推荐阅读
- 微信号为什么会被封
- 闲鱼买东西被骗怎么办,怎么举报卖家
- 怎样才能刺激毛囊生发
- 什么是网红气球 网红气球为什么被禁
- 猫在被子上尿怎么办
- 如何让自己的公众号被别人搜索到
- 被电子眼抓到了怎么办
- 每个福建人,都是被煲汤耽误的魔法师?
- 被誉为东方塑像馆的是什么石窟 哪个石窟被称为东方塑像馆
- 被野象围攻怎么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