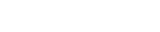文章插图
每种具体犯罪的既遂标准都是不同的,而且非常复杂,诸如抢劫、盗窃、绑架等罪名的既遂成立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界的讨论也比较多,所以针对不同犯罪的既遂还是在适当的时间有必要逐一探讨一下 。。总括 刑法分则每一罪状性条文的背后必然存在着立法者所意图保护的合法权益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四百余种犯罪,每一罪名都有其所欲保护的特定权益 。(注:需要说明,强调每一犯罪都会侵犯特定的权益,并不意味着各种犯罪侵犯的权益各有不同 。因为刑法对行为的“犯罪化”是依据多种标准而确定的 。如同样都是侵犯财产所有权,盗窃、抢夺和诈骗就是依据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区分的 。另外还需要指出,每一个罪背后并不必然只保护单一权益,相反,根据需要刑法常常可以在一罪名上设置双重甚至多重权益 。如抢劫罪,其保护权益就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两方面 。)如杀人罪,刑法所保护的权益为生命权;脱逃罪所保护的权益是国家的监管秩序;贪污罪所保护的权益为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等等 。既然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益,那么刑法分则条文在每一个罪设置上所意欲保护的合法权益(客体)是否发生实际损害,当然就成为犯罪既遂认定的根本标准 。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每一种犯罪所能造成的具体权益损害的刻画,便成为司法操作中识别犯罪既遂的基本标准 。在确定犯罪既遂的各种具体类型时,均应当以行为规律性地必然会对具体权益引发的某种实害为着眼点,只不过实害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因此,认定犯罪既遂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就是准确领会并合理解释刑法在各具体罪名中所意欲保护的客体的内容 。以此为标准,便可以解开刑法学界一些长期争论不休而终无定论的问题 。如抢夺犯为摆脱追捕而将赃物扔进河中,如果能够确认刑法的目的就是保护合法权益,那么采取被害人的财物受到实际损失作为既遂标准则无疑是合理的选择——因为所有人的财物一旦失去控制(抢夺的另一面即是失控)而被他人处置,则意味着刑法设立抢夺罪所意欲保护的所有权受到实际损害,因而是犯罪既遂 。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得到财物、如何处置,已经同刑法保护权益的意旨相去甚远而并无太大的考查价值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与犯罪既遂形态相关的几个关键名词: 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和阴谋犯 。1.行为犯 。通说认为,只要存在“行为”即为既遂,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 。此说的失误在于:行为犯的标本形态若与行为所造成的实害无关,那对该类行为作犯罪处理的依据何在?显然,行为犯中是当然包含着某种实害的,通说在对其阐述时发生了重大的认识偏差 。试以行为犯中的典型个罪诬告陷害罪为例 。通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诬告陷害行为,不管被诬陷人是否被打入冤狱,均不影响既遂的成立——行为的本态即为既遂状态,既遂同危害结果无关 。若对该罪作细致分析,便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诬告陷害行为必然产生的社会危害并不在于被诬陷人被打入冤狱,而在于对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妨害——诬告行为一经实施,必然造成司法机关的忙于应对;而一旦被诬陷人落入冤狱,其直接责任人显系司法机关而非诬告人 。诬告陷害罪必然侵犯的直接客体仅为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而并非被诬陷人的人身权利 。我国现行刑法接续古代刑法“诬告反坐”的惯例,将诬告陷害罪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其在个罪的体系安排上本身就属不当,由此而对刑法理论界形成误导 。行为犯的特点就在于行为一实施便必然产生实害——危害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附属于已然的行为存在,并且危害结果呈一种不甚明显的隐型状态 。在对行为犯的分析和把握上应高度注意这一点 。2.结果犯 。首先须阐明一点,刑法学中的“结果犯”一术语,同时表征着两方面的不同含义,在逻辑学中该现象被称为“同一语词表达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内涵及外延)” 。在犯罪构成基本要件的阐述中使用“结果犯”一术语,是指不符合该结果要件的规定性则行为不构成犯罪——即无结果则无犯罪,是在罪与非罪的意义上理解概念,如过失犯罪的成立一般均以实害结果的出现为必备条件 。故此,对该意义的结果犯可称其为“构成结果犯” 。而在犯罪的终了形态的讨论中使用“结果犯”一术语,则是指在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确定犯罪属于何种形态的问题,是在犯罪的形态层面上理解概念 。为同前一概念区别,可表述为“形态结果犯” 。所谓形态结果犯,是指犯罪完成形态的成立以实害结果的发生为必备条件,换言之,实害结果的不出现则只成立未完成形态,不存在结果犯 。在形态结果犯中,行为与结果呈分离状态——通常情况下行为一经完成,结果也就相继发生;少数情况下或者行为尚未完成故结果不发生,或者行为实施完毕但结果仍未发生(如投毒后被害人并未食用) 。故意杀人、抢劫、强奸一类犯罪,均是生活中多发而又非常典型的形态结果犯 。行为及其实害结果的观念映像,在形态结果犯的立法设计和理论构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类情况在犯罪构成的表述上,均不会有结果要件的要求(结果完全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而只影响形态的类型),但危害结果活生生血淋淋的鲜明意象却始终强烈地映现在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观念之中——无须文字描述或理论刻画便自然而然地会根据既往生活秩序形成恰如其分的处置方案 。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的“犯罪结果发生说”便是对这类现象的经验总结,能够较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具体到个罪中,行为人通过罪过发动行为所“明知”且“希望或放任”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便是区分犯罪的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具体标准 。这里有必要纠正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对构成结果犯与形态结果犯各自内涵的错误理解 。如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盗窃罪既遂标准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就盗窃罪而言,行为人一般在主观上追求“多多益善”,但如果实际上只盗得少量财产,则构成盗窃罪未遂 。笔者认为,把刑法原本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犯罪成立条件理解为仅仅是既遂的成立条件(“数额较大”被解释为属于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完全是对刑法条文的误解 。诚然,行为人在具体个案中究竟能盗得多少财产往往是由偶然因素所决定,在肯定罪过无异的情况下,刑法仅因数额的多少而作出罪与非罪的不同规定确有不公正之嫌 。然而,不能因此一点而就责备刑法 。事实上从全局看,这是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要求 。现实生活中盗窃行为数量太大,就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状况根本不可能一一犯罪化 。采取以数额定性的方法,从而将大部分盗窃行为压回到行政法规去简化处理,无疑是适当的(尽管如此,盗窃罪在数量上仍居刑案之首) 。这也是我国刑法为何对相当一部分犯罪采取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重要原因 。既然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必要条件,因此,盗窃罪是构成结果犯,而非形态结果犯 。盗窃罪原则上不存在未遂问题 。类似情况还有故意伤害罪、大多数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等等 。3.危险犯 。关于危险犯,通说认为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其主要理由是: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立法标本,犯罪的未遂、中止、预备是由刑法总则加以规定 。既然刑法分则将危险犯用单列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并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可见危险犯就是既遂犯 。然而这一理由是难以立足的:(1)危险犯与实害犯的主观罪过内容完全相同,即都是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 。如果将危险犯看成是既遂犯,那么实害犯就只能是其结果加重犯 。然而,这完全混淆了结果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区别 。须知,一般而言,结果犯之结果是本罪之结果,而结果加重犯之加重结果则是他罪之结果 。(注: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2)把危险犯视为是既遂犯,便自然排除了对中止犯的认定 。这无法起到促使犯罪分子及时中止犯罪的作用,与现代刑法奖励中止犯的基本理念相悖 。笔者认为,危险犯并不属于既遂犯,而只不过是与之相对应的实害犯的未遂犯 。就此意义而论,危险犯并没有其独立的价值,而仅仅是法律对某些具有特别重大危害的实害犯的未遂形态的一种专门规定及称谓而已 。立法者之所以对危险犯作如此规定,无非是要突出打击的重点,其目的有三:一是提示司法机关对那些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即使未造成实害结果,也应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对这类未遂犯罪(危险犯)直接依照独立的法定刑裁量即可,而不必再引用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考虑从宽处罚 。三是告诫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不得实施此类犯罪,否则即使未有实害结果同样要定罪并处以较重刑罚 。(注:尽管立法对危险犯以单列条款加以规定突出了打击的重点,然而其在现实中暴露出的缺陷也日益严重 。如前不久在某地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被告人王某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将载有四百多斤炸药的“桑塔纳”轿车开往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并将导火线点燃,所幸的是,因导火线中间段潮湿而未能引爆,从而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很显然,就现有刑法规定来说,很难以第115条处罚王某,相反,只能以第114条定罪,最高处10年有期徒刑 。然而,无论是从主观罪过还是现实危害上看,王某的行为均可谓罪大恶极,判处10年有期徒刑难言罪刑相称 。倘若依照笔者的观点,认为危险犯属实害犯的未遂形态,则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一难题 。因为依照刑法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可以”不等于“应当”,对于上述王某的行为完全可以,事实上也应该依照实害犯的法定刑处罚,唯此,才能体现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同时也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 。) 4.阴谋犯 。阴谋犯一般只在涉及国事的犯罪中出现 。1979年刑法中曾使用“阴谋”的字眼以描述某些犯罪的客观行为特征;新刑法虽未使用“阴谋”一词,但其实仍有类似的规定 。通说认为,就阴谋犯而言,行为人只要实施预备行为即构成既遂的犯罪形态 。理由是阴谋犯是危害性十分严重的犯罪,为了进行有效的社会预防,刑法把这类犯罪的完成形态(既遂)往前推移至预备行为的实施阶段 。若真如此,既遂还有何标准可言?无可否认,阴谋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理应从重打击 。然而从重打击未必一定要说成是既遂,仿佛在通说论者看来,不把阴谋犯说成是既遂犯,对其从重打击就显得底气不足 。其实这种杞人忧天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 。须知,我国刑法并不仅仅处罚既遂犯,而且还处罚未遂、预备,乃至中止犯 。我们又何必仅仅为了强调对某一类犯罪从重打击而破坏应有的理论体系呢?事实上刑法单列“阴谋犯”条文的规定同样是基于上述危险犯的理由 。从实际情况看,阴谋犯一般只处于预备阶段便因意志以外原因而终了,很难进入“着手”实施的未遂阶段,更无可能达到目的造成实害以形成既遂 。这是因为任何国家评价犯罪的主体都是取得统治地位的集团,倘若阴谋犯真已既遂,那么评价犯罪的主体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阴谋行为”也因价值评判的主体和标准的变化而演变成了“功劳行为”,所谓“成王败寇”即是此理
推荐阅读
- 犯组词 汉字犯怎么组词
- 打工同居是否犯法 打工可以同居吗
- 博美犬六大禁忌 赶紧看看你犯了那个
- 侵犯个人信息立案标准是什么
- 消费者行为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是消费者行为
- 辣椒怎样种结果又多又大
- 手机上怎么查车辆违章 交通违章行为很严重机动车违章查询方式有哪些
- 哪些行为属于违反消费者保障服务质量规定?
- 犯太岁化解方法 犯太岁化解方法是什么
- 行为乖张什么意思 乖张的含义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