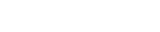20е®ҝдё–зәӘ80е№ҙжңҲзҡ„дёҖеӨ© пјҢ дёҖеҗҚй…ҚеҒ¶еҘіеҺ»з—…йҷўжҺҘз®ЎзҷҢз—ҮжүӢжңҜ пјҢ жүӢжңҜеҫҲеҪ“дҪңеҠҹ пјҢ жүҖжңүзҡ„зҷҢзҒ¶йғҪиў«еҲҮйҷӨдәҶ гҖӮ 然иҖҢеҮ дёӘзӨјжӢңеҗҺ пјҢ еҘ№ж„ҹеә”жңүдәӣдёҚеҗҲй”ҷиҜҜеҠІ гҖӮ еҘ№еӣһеҲ°еӨ–科еӨ§еӨ«йӮЈиҫ№ пјҢ еӨ–科еӨ§еӨ«и®©еҘ№е®үеҝғзҷҢз—Үе·Із»Ҹж¶ҲйҖқдәҶпјӣеҘ№еҸҲеҺ»е’ЁиҜўдәҶеҝғзҗҶеӨ§еӨ« пјҢ еҝғзҗҶеӨ§еӨ«з»ҷеҘ№ејҖдәҶжҠ—жҠ‘йғҒиҚҜ гҖӮ
然иҖҢиҝҷдёҖеҲҮж— жөҺдәҺдәӢвҖ”вҖ”еҘ№и¶ҠжқҘи¶ҠзЎ®дҝЎжң¬иә«е‘ҪдёҚд№…зҹЈ гҖӮ еҘ№д»ҺеӨҙи§ҒдәҶеӨ–科еӨ§еӨ« пјҢ еӨ§еӨ«еҶҚж¬ЎжҠҡж…°еҘ№вҖңдёҖеҲҮйғҪеҫҲеҘҪвҖқж—¶ пјҢ еҘ№зӘҒ然и„ұеҸЈиҖҢеҮәпјҡвҖңй»‘иүІзҡ„е·Ҙе…·пјҒжӮЁжІЎжңүиҺ·еҫ—й»‘иүІзҡ„е·Ҙе…·пјҒвҖқ
еӨ§еӨ«е‘ҶеӨҙе‘Ҷи„‘ пјҢ еӣ дёәд»–иҝҳи®°еҫ—еңЁжүӢжңҜж—¶д»Ј пјҢ д»–жӣҫж— ж„Ҹж Үзҡ„зӣ®зҡ„еҗҢдәӢеҹӢжҖЁжң¬иә«жөҙе®ӨйҮҢйҡҫд»Ҙж–ӯж №зҡ„й»‘иүІйңүиҸҢ гҖӮ зҷҢзҒ¶еңЁиҝҷеҗҚй…ҚеҒ¶еҘізҡ„и…№йғЁ пјҢ жүӢжңҜж—¶д»ЈеҘ№еӨ„дәҺе…Ёиә«йә»йҶүзҠ¶еҶө пјҢ е°Ҫз®ЎеҰӮж–Ҝ пјҢ еӨ§еӨ«зҡ„иҜқдјјд№Һе·Із»Ҹз•ҷеңЁеҘ№и„‘жө·йҮҢдәҶ гҖӮ еҪ“еҘ№еҫ—зҹҘжүӢжңҜдёӯеӨ§еӨ«зҡ„иҝҷж®өеҜ№иҜқеҗҺ пјҢ еҘ№зҡ„з„ҰзӮҷдҫҝзғҹж¶Ҳдә‘ж•ЈдәҶ гҖӮ
еңЁгҖҠйә»йҶүпјҡйҒ—еҝҳзҡ„зӨје“Ғе’Ңж„ҸиҜҶд№Ӣи°ңгҖӢпјҲAnesthesia: The Gift of Oblivion and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пјүдёҖд№Ұдёӯ пјҢ зҫҺеӣҪеҝғзҗҶеӯҰ家дәЁеҲ©В·иҙқеҶ…зү№пјҲHenry Bennettпјүж Үзҡ„зӣ®зҡ„жҫіеӨ§еҲ©дәҡйҮҮи®ҝдәәе‘ҳеҮҜзү№В·з§‘е°”-дәҡеҪ“ж–ҜпјҲKate Cole-Adamsпјүи®Іиҝ°дәҶиҝҷдёӘж•…дәӢ гҖӮ 科尔-дәҡеҪ“ж–Ҝд»Һйә»йҶүеёҲе’ҢеҝғзҗҶеӯҰ家йӮЈиҫ№еҗ¬иҝҮиүҜеӨҡиҝ‘дјјзҡ„ж•…дәӢпјҡжҳҫ然 пјҢ дәә们еңЁйә»йҶүзҠ¶еҶөдёӢд»ҚиғҪеҗ¬еҲ°еЈ°йҹі пјҢ иҖҢдё”еҸ—еҲ°иҝҷдәӣеЈ°йҹізҡ„еҪұе“Қ пјҢ еҚідҪҝ他们жң¬иә«е№¶дёҚи®°еҫ— гҖӮ
дёҖеҗҚй…ҚеҒ¶еҘіеңЁеӯҗе®«еҲҮйҷӨжңҜеҗҺеұҘеҺҶдәҶжҒҗжҖ–зҡ„жҺүзң пјҢ еңЁеҗҺжқҘзҡ„еӮ¬зң жІ»з–—дёӯеҘ№еӣһеҝҶиө·йә»йҶүеёҲжҒ¶дҪңеү§иҜҙ пјҢ еҘ№е°ҶвҖңйҷ·е…ҘзҒӯдәЎиҲ¬зҡ„зқЎзң вҖқ гҖӮ еҸҰдёҖеҗҚжӮЈиҖ…еңЁдёҖдёӘе°ҸжүӢжңҜеҗҺжғіиҮӘжқҖ пјҢ йҡҸеҗҺеҘ№и®°иө· пјҢ еҪ“еҘ№иәәеңЁжүӢжңҜеҸ°дёҠзҡ„ж—¶иҫ° пјҢ еҘ№зҡ„еӨ–科еӨ§еӨ«жғҠеҸ«йҒ“пјҡвҖңеҘ№еҫҲиғ– пјҢ дёҚжҳҜеҗ—пјҒвҖқ
еңЁ20е®ҝдё–зәӘ90е№ҙжңҲ пјҢ еҫ·еӣҪ科еӯҰ家з»ҷ30еҗҚеҚіе°ҶиҝӣиЎҢеҝғи„ҸжүӢжңҜзҡ„жӮЈиҖ…жҲҙдёҠиҖіжңә пјҢ 并еңЁжүӢжңҜиҝҮзЁӢдёӯж’ӯж”ҫдәҶгҖҠйІҒж»ЁйҖҠжјӮжөҒи®°гҖӢзҡ„еҲ еҮҸзүҲжң¬ гҖӮ жӮЈиҖ…ж— дёҖи®°иө·иҝҷ件дәӢ пјҢ дҪҶдёҚд№…еҗҺеҪ“иў«й—®иө·вҖңзӨјжӢңдә”вҖқиҝҷдёӘиҜҚж—¶ пјҢ 他们йЎҝж—¶жғіеҲ°зҡ„йғҪжҳҜд№Ұдёӯзҡ„ж•…дәӢ гҖӮ
1985е№ҙ пјҢ иҙқеҶ…зү№иҰҒжұӮжҺҘз®ЎиғҶеӣҠжҲ–и„ҠжҹұжүӢжңҜзҡ„жӮЈиҖ…дҪ©еёҰиҖіжңә пјҢ 他们еҗ¬еҲ°зҡ„жҳҜиҙқеҶ…зү№иҜҙзқҖпјҡвҖңеҪ“жҲ‘жқҘе’ҢжӮЁжҺӘиҫһж—¶ пјҢ жӮЁе°ұиҪ»ж‘ёжӮЁзҡ„иҖіжңөвҖқпјӣеҜ№з…§з»„еҗ¬еҲ°зҡ„еҲҷжҳҜжүӢжңҜе®ӨйҮҢзҡ„еЈ°йҹі гҖӮ еҪ“жӮЈиҖ…们и§Ғд»–ж—¶ пјҢ йӮЈдәӣеҗ¬еҲ°жҺӘиҫһзҡ„дәәи§Ұж‘ёиҖіжңөзҡ„йў‘зҺҮжҳҜеҜ№з…§з»„зҡ„дёүеҖҚ гҖӮ
еңЁд»ҚжҳҜйқ’е°‘е№ҙзҡ„ж—¶иҫ° пјҢ 科尔-дәҡеҪ“ж–Ҝе°ұиў«иҜҠж–ӯдёәи„Ҡжҹұдҫ§ејҜ пјҢ еҘ№иө·еӨҙе®іжҖ•е°ҶжқҘеҸҜиғҪиҰҒжҺҘз®Ўж”№жӯЈи„ҠжҹұејҜжӣІзҡ„еҚұйҷ©жүӢжңҜпјӣеҲ°дёӯе№ҙж—¶ пјҢ еҘ№зҡ„й©јиғҢи¶ҠжқҘи¶ҠдёҘйҮҚ пјҢ еҘ№ж„ҸиҜҶеҲ°жүӢжңҜжҳҜдёҚжҲҗйҒҝе…Қзҡ„ гҖӮ жҲ–и®ёжҳҜдёәдәҶйҷҚжңҚжғҠйӘҮ пјҢ еҘ№д»Һ1999е№ҙиө·еӨҙз ”з©¶йә»йҶү пјҢ еңЁиҝ‘д№ҺдәҢеҚҒе№ҙзҡ„е°ҪеҠӣеҗҺ пјҢ еҘ№еҶҷдёӢдәҶеҜ№йә»йҶүиҝҷзүҮжҳҸй»„зјҘзјҲзҡ„жңӘзҹҘиҢғз•ҙз—ҙиҝ·гҖҒзҘһз§ҳгҖҒеҸҜйӘҮгҖҒз”ҡиҮіжҳҜе№»еҪұиҲ¬зҡ„ж‘ёзҙў гҖӮ
йҷӨдәҶйә»йҶү пјҢ иҝҷжң¬д№ҰиҝҳжҸҸиҝ°дәҶ科尔-дәҡеҪ“ж–Ҝзҡ„з«Ҙе№ҙгҖҒжҖҷжҒғгҖҒеҮ ж®өзҲұжғ…е’Ңеҗ„зұ»зІҫеҠӣдҪ“йӘҢе’ҢдҝқеӯҳеҚұжңәвҖ”вҖ”дёҖз§ҚжөҒиҗҪдёҚе®ҡиҖҢеҸҲж— ж—¶дёҚеңЁзҡ„з»„еҗҲ пјҢ жіЁе®ҡиҰҒе”Өиө·иў«йә»йҶүзҡ„еҝғзҒө гҖӮ еҘ№и®°е®һдёӢеҫҲеӨҡиў«йҒ—еҝҳзҡ„еұҘеҺҶе’ҢдёҚжӣҫж„ҹи§Ұж„ҹжҹ“иҝҮзҡ„жғ…ж„ҹ пјҢ иҝ·жғ‘зқҖпјҡеңЁеӨҡеӨ§ж°ҙе№ідёҠ пјҢ жҲ‘们已з»Ҹд»ҘдёҖз§Қйә»йҶүзҡ„зҠ¶еҶөзіҠеҸЈзқҖе‘ўпјҹ
йә»йҶүеёҲжҸҸиҝ°з—…дәә们еұҘеҺҶйә»йҶүзҡ„еҮ дёӘйҳ¶ж®өпјҡд»Һиҝ·жҺүеҒҸеҗ‘ пјҢ еҲ°и°өеҰ„ пјҢ жңҖеҗҺиҝӣе…ҘжүӢжңҜзҠ¶еҶө гҖӮ еҪ“жҲ‘们иҝӣе…Ҙйә»йҶүж—¶ пјҢ 他们з»Ҹз”ұиҝҮзЁӢзӣ‘жөӢи„‘з”өжіўжқҘж»ҙе®ҡвҖңйә»йҶүйёЎд»ҺеӨҙиҮіе°ҫй…’вҖқ пјҢ д»ҘзЎ®дҝқеҲ©з”Ёзҡ„й•ҮйқҷеүӮдёҚдјҡиҝҮеӨҡжҲ–иҝҮе°‘пјҲе…ёеһӢзҡ„вҖңйёЎд»ҺеӨҙиҮіе°ҫй…’вҖқеҗ«жңүдёҖз§Қжӯўз—ӣиҚҜгҖҒдёҖз§ҚиӮҢжқҫиҚҜе’ҢдёҖз§ҚеӮ¬зң иҚҜ гҖӮ иӮҢжқҫиҚҜеҸҜд»ҘйҳІжӯўжүӢжңҜеҲҖеҲ’иҝҮж—¶иӮҢиӮүзј©зҹӯ пјҢ ж—©жңҹзҡ„иӮҢжқҫиҚҜжқҘеҺҶдәҺз®ӯжҜ’ пјҢ жҳҜеҚ—зҫҺжҙІе…өеЈ«ж¶ӮеңЁеј“з®ӯдёҠз”Ёд»ҘеҢ№ж•Ң欧жҙІдәәзҡ„жҜ’иҚҜ пјҢ иҖҢеӮ¬зң иҚҜеҸҜд»ҘдҪҝдәәжҺүеҺ»ж„ҸиҜҶ гҖӮ пјүдҪҶеҚідҪҝйә»йҶүеёҲиғҪд»ҘзІҫж№ӣжүӢжі•ж“ҚдҪңйә»йҶүеҷЁжў° пјҢ 他们еҜ№иҝҷдәӣиҚҜзү©иғҢеҗҺзҡ„жңәеҲ¶д»Қ然дёҖзҹҘеҚҠи§Ј гҖӮ
вҖңжҳҫ然 пјҢ жҲ‘们еҸҜд»ҘејҖе…·йә»йҶүиҚҜ пјҢ 并且иғҪеҫҲеҘҪең°иҠӮеҲ¶е®ғ пјҢ вҖқдёҖдҪҚеӨ§еӨ«е‘ҠиҜү科尔-дәҡеҪ“ж–Ҝ пјҢ вҖңеҸҜжҳҜеңЁзңҹжӯЈзҡ„е“ІеӯҰе’ҢеҝғзҗҶеӯҰеұӮйқўдёҠ пјҢ жҲ‘们д»ҚдёҚзҹҘйҒ“йә»йҶүзҡ„жңәзҗҶ гҖӮ вҖқй—®йўҳзҡ„ж №жәҗеңЁдәҺ пјҢ жІЎжңүдәәзҹҘйҒ“жҲ‘们дёәд»Җд№Ҳжңүж„ҸиҜҶ пјҢ иҝҷе°ұд»ҝдҪӣиӢҘжҳҜжӮЁдёҚзҹҘйҒ“еӨӘйҳідёәдҪ•еҚҮиө· пјҢ е°ұйҡҫд»ҘиҜ йҮҠе®ғдёәдҪ•еҸҲдјҡиҗҪдёӢ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ҰӮдҪ•и®©з…§зүҮеҠЁиө·жқҘ
- еҚҺдёәжүӢжңәжЎҢйқўеҰӮдҪ•ж·»еҠ ж—¶й’ҹе°Ҹе·Ҙе…·
- PSжӣҝжҚўйўңиүІж–№жі•
- жҖҺд№Ҳжүҫеӣһиҫ“е…Ҙжі•еӣҫж Ү
- PSжёҗеҸҳе·Ҙе…·жҖҺд№ҲдҪҝз”Ё
- з»қең°жұӮз”ҹеҲәжҝҖжҲҳеңәжүӢжёёеҠ йҖҹж—¶ж— жі•и·іи·ғжҖҺд№ҲеҠһ
- ж—¶е°ҡиҢ¶иүІ
- Word еҰӮдҪ•ж·»еҠ еёҰж—Ҙжңҹж—¶й—ҙзҡ„йЎөзңү
- еҚҺдёәжүӢжңәжЎҢйқўеҰӮдҪ•ж·»еҠ е’Ң移йҷӨвҖңеҸҢж—¶й’ҹвҖқе°Ҹе·Ҙе…·
- еҚҺдёәжүӢжңәжЎҢйқўеҰӮдҪ•ж·»еҠ е’Ң移йҷӨж—¶й’ҹе°Ҹе·Ҙе…·